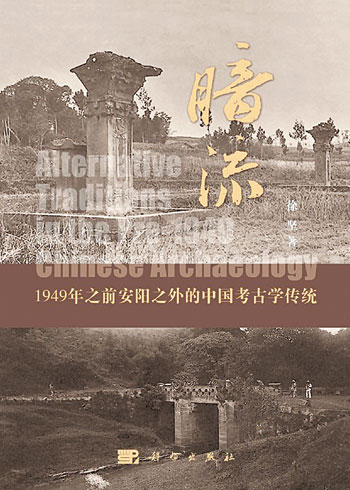 这并不是一本按常规出牌的考古学术史著作。 从字面上看,《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Alternative Tradition in the Pre-1949 Chinese Archaeology)本身就是一个“另类”的题目。一方面,作者自言:“暗流传统是单线式进化主义考古学史写作界定的术语”,以旧语发新意,丰富了主流线索的言外之意。另一方面,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是全书的理论主线;通过反思考古学史的视角和写作,展现中国考古学的多来源、多环节和多线索的景象,从而展示考古学史和考古学研究之间的互动和反射关系,这正是全书写作主旨的关键所在。 但作者的雄心远不止于此。学术史的认知不应停留在学人交往的陈述,又或是著述研究的罗列,这已是屡见不鲜的老生常谈;以学科分野为径,探求知识转型,尤其是基础知识、技法乃至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几乎是所有此类学术流派研究的不二法门。然而学术史的情怀该往何处去,学科学术史的范式如何建立,就这些问题学者之间的各循因由,破而能立亦有境界高下之分。作者的“利器”固然与其考古学、人类学素养的训练密切相关,但其反思考古学史的视角却突破了学科的园囿,回到“历史学的考古学”,从多维向度的学术史情境中首次展示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史的多元全景。 作者在绪论《暗流:超越安阳》中指出,考古学史中的“暗流”具有多种标准,其中包括:人员和机构、“科学”和“非科学”、及实证和理论之别。尽管这三个标准囊括人脉、体系和学理要素,但其界定的范围、层次不一。就书中选取分析的个案而言,这三个标准有诸多重复叠加的细节。分类越清晰,标准定性的“合理化”解释反而越模糊。诚如多元观念带来范式转型的启发一样,我们仍热切期望更为尽善其美、或者是更有说服力的分流界限的设定——但至少在以安阳为“主流”的统一标准上,暗流的脉络开始浮出水面。 安阳何以成为主流,一是时间节点的历史选择,二是中国考古学奠基进程中的人事和情势。作者在第一、二章中反复强调安阳历经的时间和空间转换,既有平行的安阳:中央与地方、科学发掘与寻宝盗掘、本国与他国在发现、保管和阐释上的冲突与斗争;亦有安阳之外:以公私收藏和相似、相近遗址为个案,在研究主题的扩张和方法的更新,从而以平视的眼光了解安阳传统的多种面相。诚然,安阳的特殊价值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枚标杆;但史语所的安阳不是独一无二的展示,考古学的学科传统发展在作者厘定的三个标准下有了更长足的个案分析:这些同样是中国考古学基础知识、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的重要来源。在方法论上,作者明确地指出:竭泽而渔的个案分析绝非治学术史的良法,考古学的考古学作业方式须回到学术史的情境当中方可实现。具体而言,则是作者称之为文化人类学中的“回访”(revisit)方法;多个层面的“回访”则构成了考古学史及考古学中的“深描”方法。 基于此,“回访”的技术操作并不具备任何的学科信仰。其更重要的目的,在于“解释早期工作特定的作业程序和理论预设”。作者努力避免将“暗流”演变为另一种主流,从而标示出暗流传统的去污名化,以及建立学科学术史通则性意义的漂亮解释。这就是全书问题意识形成的基本框架。 暗流同时亦是众流。作者在第三章中援引了博物馆、研究机构、大学和独立的学术团体等的工作为佐证,集中对三个个案:云南博物馆、黄花考古学院和考古学社进行诠释,借以说明考古学理解中的多元特征。第四章中,讨论了云南的本土学人通过器物群和地面遗迹构建的具有乡土史倾向的区域考古学类型。第五章中,讨论了以铜鼓为中心的民族考古学,是为具有人类学或者民族学倾向的考古学类型。以上讨论的考古学类型,其共同点在于区域集中分布在今日中国的非中心地区。同时,这也是传统中国的四裔之地。一直以来,受制于地理和政治的“边缘”,考古学的多元长期无法得到正视,更勿论被遗忘、被忽视甚至被误读的历史和文化。彰显缺失的学统,不仅是复原已经被中国考古学史所遗忘的记忆。个案的“发现”从不也不应止步,而是系统重构中国考古学史多元全景的崭新开始。 进一步地,作者在第六、七章中讨论了两条曾经不入考古学家法眼的线索:盗宝私藏和古董市场流通,复原了更多的暗流图景。令人欣喜的是,自十九世纪以来大批被纳入西方艺术系统的公私收藏,成为我们了解中国考古学暗角的灵光之匙。此外,1949年之前的考古学研究,在实证和学理上有许多东西方相结合的绝妙个案。不同的学术传统在第八章的崖墓一题中汇合互动,揭示了更为晚近年代的考古学术史情境。第九章的考古理念入华,无疑更像是一个开放式的命题,被置放于全球考古学发展一支中进行考虑。 正因为范围所涉之广大,问题洞察之复杂,暗流既相互抵牾,亦各种叠合。作者清醒地意识到,暗流个案无法穷举。重新发现暗流并不仅是为了正名,而是反思主流传统何以定义。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作者认同的暗流视角即后过程主义考古学。 新考古学对当代考古学理论贡献良多,但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本位和互动一直争议不断。崔格尔(Trigger)就提出考古学阐释应该回归到历史学的阐释之中。相应地,霍德(Hodder)则表述为:“物质文化是有意义构成的;行为者必须成为物质文化和社会变迁模式的一部分;尽管考古学独立存在,但与历史学保持最密切的纽带关系”。作者更为明晰地指出了这种纽带关系,即:在历史特定主义的情境分析中,对多元文化的考古学面貌的关注,以及对考古学史上的多元传统的认识几可同步。在此意义上,暗流传统的聚合离散,合力构成了回归历史学的考古学的最佳门径。 1972年,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e)发出掷地有声的呼喊:“考古学就是作为考古学的考古学”。而作者自1996年便开始追溯的考古学史寻根之路,终于以“暗涌的深流”在中国考古学个案中写下完美的一笔。 (《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徐坚著,科学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定价:68元)(《中国文物报》2012年5月4日4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