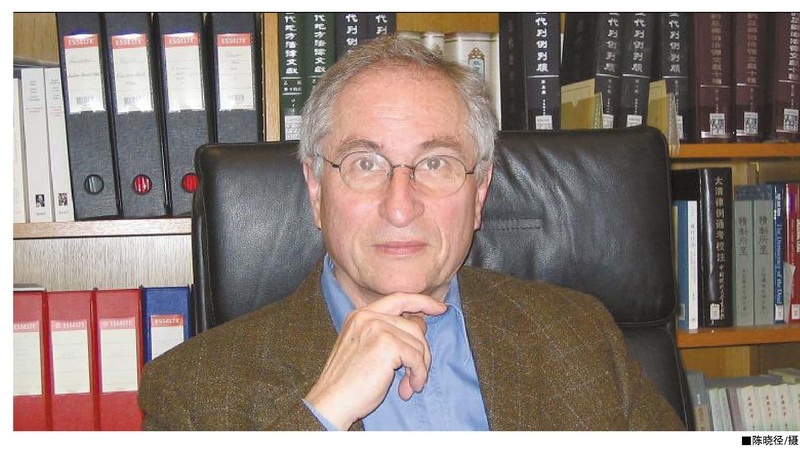 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法国著名汉学家,1944年生于法国东部城市格莱,1988——1991年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研究主任,1991年至今在法兰西学院任教,执掌中国现代史教席。在40余年的汉学研究生涯中,魏丕信著作甚丰,其中,最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当属他的博士论文——《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成书于1980年,2003年译成中文出版)。此外,魏丕信还出版了4部专著,发表重要学术论文数十篇。魏丕信最近的著作是与法学家德勒马斯-马蒂(Delmas-Marty)女士合编的《中国与民主》一书,该书于2007年由巴黎费雅出版社出版。目前,他正在酝酿新作——《中国帝制时期的官箴书选集》。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使魏丕信为中国的史学研究者所熟知,近期,笔者在法兰西学院聆听了魏丕信教授的中国现代史课程,并对他进行了专访。他以历史学家所独有的冷静和睿智,传递出对中国封建王朝晚期官僚制度的独到见解,表达了他对法国汉学研究的关注,并从历史的视角评析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从语言兴趣转向历史研究 陈晓径:您是著名的汉学家,47岁就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进入法兰西学院执教,在汉学领域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汉学,尤其是选择研究清朝历史?并请简要介绍一下您的治学经历。 魏丕信:关于我对汉学的选择,当初并没有下定很大决心,只是想选一个冷门的专业。我从古典文化起步,修习了拉丁文、希腊文,同时也在巴黎学习汉语并产生一定兴趣,而且不久之后就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找到研究汉学的机会。 当时还是20世纪60年代初,汉学远远没有现在那么热门,研究起来很困难;全法国仅有一所学校可以学习汉语,那就是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即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的前身)。在汉语课程开设的首年,仅有60人选修了这方面的课程,而现在该校一年级中文系的学生已达1200人之多。真是今非昔比!我在那里学习了3年。当然,学习中文是没有止境的,除了正规的课程训练之外,我还花了大量的时间自学。 后来,我转向中国历史研究;并结识了索邦大学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还听过他的课,正是他把我引向清朝历史研究。我知道自己对古代历史不太感兴趣,曾经想研究汉语语言,但后来发现兴趣不大,最终选择了清代历史研究。 学业结束后,我很快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即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前身)担任助教,与比我年长的同事米歇尔·卡迪埃(Michel Cartier)一起开展中国人口史研究。这一项目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中寻找资料。巴黎关于这方面的地方志资料非常丰富,是整个欧洲最全的。20世纪70年代初,我曾到日本东京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最终发现中国封建王朝晚期的官僚制度是自己的研究兴趣所在。 关注中国官僚制度的实际运作 陈晓径:您自从进入法兰西学院执掌中国现代史教席以来,连续开设了不少课程:1999—2003年花4年时间讲解中华帝国晚期的执政者形象,2004—2008年花4年时间分析中华民国时期的工程师、慈善家和军阀,从2010年3月到现在,您又在探讨从明朝到清朝的朝代更迭。请问您开设这些课程的思路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否反映了您研究领域的变化? 魏丕信:其实之前我还开设过别的课程。1992—1995年,我开设的课程是“帝国晚期的交流和动员”;1996—1997年讲的是“经济思想和市场”。我开设课程的思路始终是一致的,都是研究“中国官僚制度”。我的博士论文《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探讨中国官僚制度究竟怎样运作: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要搞清楚这一制度的实际运作。我近40年的研究都没有绕开“中国官僚制度”这一主题。比如,近15年来(当然,这项工作已接近尾声),我和同事们都在整理中国古代官员的手稿书目——“官箴书”;我到处搜集材料,搜集了来自中国、日本、美洲等地的很多材料。我喜欢阅读第一手资料——西方有些学者向来只读二手资料,然后重复同样的东西。 中国的官僚制度是我最感兴趣的,但我也会以此为中心,展开一些相关研究。2004—2008年我开设的课程重点分析中华民国时期的工程师、慈善家和军阀,起因是我一直偏爱水利史研究,希望清楚地了解中国水利设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而对水利学家李仪祉(1882—1938)主持修建陕西泾惠渠(前身为郑国渠)的研究,就不得不参考李仪祉所处的政治环境及军阀、慈善家等因素的影响。水利设施建设也是中国官僚制度的运作中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因此,我开设的所有课程的总体思路都是中国官僚制度的实际运作,以及这一制度面临的问题——如何处理和人民的关系。 传统与民主并不相斥 全面了解中国历史 陈晓径:我注意到,您的著作大多涉及明、清、中华民国及其后的历史,尤以明、清为重,请问您为何对明、清情有独钟?您书中提到,明朝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民主的萌芽;而在中国,人们经常说明、清时期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开始,请问您选择明、清作为主要研究领域,是否与这些观点有关? 魏丕信:不,与这些观点没有关系,我研究清代历史主要出于个人兴趣。至于与民主萌芽的关系,我是想通过历史研究,厘清一些现象:比如中国的民主,或者现代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我和同事、法学家德勒马斯-马蒂女士举办过一次研讨会,邀请历史学家、中国当代问题专家研究“民主”这一概念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含义。人们常说中国传统是与民主不相容的;我并不这么认为——任何传统都不会完全排斥民主。明朝末年,政治上很开明,有过很多次公开讨论,甚至连皇权也在论题之列;而且出现了一套相当于“宪法”的文字和实践体系,任何人——包括皇帝在内,都得遵守。这一观点并非具有独创性,但我就此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清朝末年反对帝制的革命者重新解读明末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著作,认为他们在思想上已经是民主主义者,只是清朝统治者镇压了这一思想。我并不认同这一观点——明朝末年,某些学者尚未形成完全意义上的民主思想,但中国传统中的确存在民主的元素和条件,可以被改革者利用。权利、言论自由等概念都已出现,虽然不能和18世纪西方意义上的民主相提并论,但有些元素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此外,虽然我主要研究清代历史,但要研究清代,就不能只从1644年开始研究,而至少应该追溯到明朝后半叶。从明朝到清朝,有很多主题是一脉相承的。不过,有的同行则不是这样做——他们研究清朝历史,就不愿意了解明朝发生了些什么。我对明朝感兴趣主要出于两点原因:其一,很多问题并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改变其本质;其二,明朝末年的历史非常有趣,而且资料很丰富。我近3年的课程就围绕明朝末年的私人历史而非官修历史展开。比如日记、个人记载、野史等。已经有历史学家对这些资料感兴趣了,我在台湾发现了不少重新印刷的野史,读起来总觉得很有意思。我还认为,尽管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研究每个朝代的专家,但要研究中国历史,就必须对各个朝代都有一定了解。我也喜欢唐宋时期,还和同事一起研究宋朝的历史,因而,我的研究领域并不局限于明代、清代的中国历史。我也关注清朝以后的历史。比如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史,在很多方面都与明清史不同,但非常有趣,是一个新的开端。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