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重新发明”近代中国的历史书写,仅限于中国大陆, 几乎完全排除包括港台在内的广大华文世界,读者看到书名后的预期有些落差。 此书大部分的内容是叙述“革命叙事”与“近代化叙事”,并以胡绳从“革命叙事”撤退, 证明“近代化叙事”最终压倒“革命叙事”。但在结论里用后现代的语气说, 这两种叙事基本上是历史家集体想象的产品,旨在解释以及合理化他们所想要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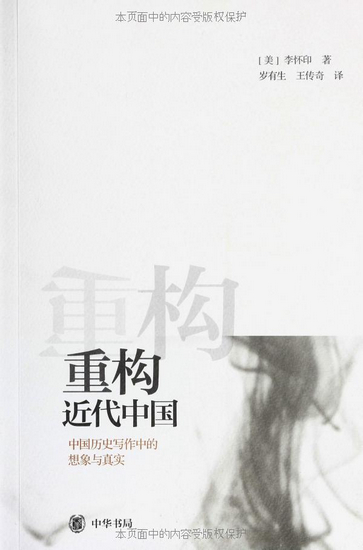 《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 李怀印著 岁有生 王传奇译 中华书局 2013年10月第一版 332页,55.00元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Huaiyin Li著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据知这本书已有中译本,书名为《重构近代中国》,但还不曾读到,本书评所据为英文原著(引文也是笔者所译)。英文本书名主题为Reinventing Modern China,直译就是“重新发明现代中国”。唯不知作者李怀印(Huaiyin Li)只是用一个时髦的字“重新发明”(reinventing),还是真要以“后现代”的概念来论述“中国的历史书写”(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如属于后者,那中国的历史书写只有“想象”(imagination),何来“真实”(authenticity)?因“后现代”以“发明”来取代现代史学所重视的“发现”,就是认为真实发生过的历史随风而逝,不可复得,所有的历史都是史家的“发明”,甚至认为历史家写历史无异于文学家写小说。通阅全书,作者不时喜用一些“后现代”的名词,但并没有真用后现代理论来写中国现代史的史学史。有鉴于作者不屑“极端革命史学”之扭曲史实,必然是相信有客观而能够信赖的历史。作者在立论上徘徊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难免令读者有不一致的感觉。 此书主要的内容是近代中国历史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书写,涵盖的时间主要是二十世纪,各章节分别为1949年以前的“民族主义史学”,1949年以前的“马克思史学”,1950年代马克思“新正统史学”之形成,毛泽东发动的“极端史学”,1980年代挑战革命正统的“新启蒙史学”,以及改革开放时代史学典范的转移。从这些章节可知,所谓“重新发明”近代中国的历史书写,仅限于中国大陆,几乎完全排除包括港台在内的广大华文世界,读者看到书名后的预期有些落差。即使仅涵盖大陆地区,百年之中史家之众、著作之多、议题之繁,也难免有挂一漏万、考虑未周之处。谨就管见所及,略作评论,未必有当,谨就教于作者与读者。 梁启超在上世纪之初,提倡“新史学”,号称史学革命,视传统史学为“帝王家谱”而否定之,欲代之以西方盛行的“国史”(national history)。而民族主义乃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西方列强也有其民族主义,且形之于史学书写,西洋史学史称之为“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史学”,而不称“民族主义史学”。近代中国受到列强侵略,“近代民族主义”自更高涨,然作者并未专注于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历史书写,却花了许多篇幅旁及1930年代主流知识分子抛弃民主自由而倾向专制独裁国家(p.38,英文本,下同),引用了不少自由派人士的政论文字,主张对内独裁,支持南京政府,对外亲善等言论(pp.60-71)。如果当时的民主与独裁之争与历史书写没有直接的关系,岂不偏离了“历史书写”的主题,不免令读者有节外生枝之感。 作者既不深探1949年前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史学,而视此一时期为“近代化叙事的开端”。所谓近代化的本质就是西化,西方国家最先近代化,成为非西方国家近代化的模式。非西方国家有其自身的文化,虽采用西方模式,其结果未必与西化同,故称之为近代化,实优于西化。然作者认为“从西化转变为近代化反映知识分子愈来愈感觉到视西方文化或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为非西方国家致富强唯一模式的谬误”(p.42)。非西方国家在二十世纪既尚未近代化或充分近代化,除了唯一的西方模式外,似无别的模式可言。更费解的是,作者认为“1930-1940年代中国近代化论者的理念,与1950-196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近代化理论极为相似,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张近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多在美国受教育,因而他们得以分享西方的近代化理论”(pp.42-43)。按1950-1960年代的近代化理论产生于二战后之西方,特别是美国,乃有鉴于殖民地时代终结后,亚、非、拉新兴国家蜂起,学者争相为之设计近代化理论。近代化理论实有丰富的内涵,而1930-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谓近代化多从字面理解,认为传统是近代化的阻力,希望中国排除阻力而能走向近代化的共同之路,迎头赶上西方国家,与1950-1960年代近代化理论并不相似。近代化理论并不认为传统是阻力;正好相反,传统往往可以成为近代化的助力,两者截然异趣。作者更犯了“时间错乱”的谬误,请问1930-1940年代中国学者如何能够受到1950-1960年代近代化理论的影响? 作者所谓“近代化叙事”的要点是着重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与改革,重视科技、精英领导等议题,而不强调帝国主义的侵略与革命运动。其实,就现代中国而言,帝国主义或革命运动无论是近代化过程中的正面或负面因素,都是无法回避而需认真对待的重大史实。作者将“近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分作两种不同的“叙事”,无非要说明对历史事件的选择与解释有异。然而就中国近代史的叙事而言,近代化项目与革命运动都应该是叙事的内容,不宜偏废。作者认为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无论在方法上或概念上创造了研究的新风格(p.45)。然而作者只是引用一人的赞美之词为证,却不进一步以自己的论证,告诉读者何以这本偏重外交史的小册子,有这样重大的学术贡献。 作者认为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是众所公认1949年之前最权威的教科书,其主旨是中国近代化的延误不在外力,而是由于内部的保守、自大、腐化,所以几乎完全不提帝国主义(p.53,p.55)。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所起的作用与影响或有争议,但其重要性之巨大却毋庸置疑。如果一部中国近代史几乎完全不提帝国主义,则其权威性至少是相当片面的。更重要的是,作者将蒋廷黻和陈恭禄视为“近代化论述”史家的代表,但在小结中又说,蒋、陈两人“在他们的书里很少或全不讨论中国在工业、交通、公共卫生、高等教育、政府系统、文学与艺术等方面的进步”(pp.72-73)。如果连这些近代化的要项都很少提及,或根本不提,算什么“近代化叙事”啊!再者,作者称这一章为“近代化叙事的开始”,但这一开始并没有于1949年终结,在港台继续发展的丰富内容,可惜开了天窗,南港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曾有庞大的中国近代化研究计划,也一笔不提。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