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1932年6月5日,廖平在家乡四川井研辞世。三百年来,四川学界积贫积弱,廖平的离世对蜀学的打击可想而知。对此,入室弟子蒙文通更会感到重任在肩。在此后的一二年间,蒙氏连续撰写《井研廖师与近代今文学》《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三篇文章,先论近代今文学,次论清代汉学,最后上升到汉代今古文学,逐级确立了廖平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为首的《井研廖师与近代今文学》一文,劈头就重申了蒙文通早年在《古史甄微》“序言”中的观点:“汉代之今文学惟一,今世之今文学有二。”在他看来,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一干常州学者,虽名为“今文学家”,实未审经今文学之真谛。 然于今古两派立说异同,其中心所在,实未之知,徒以立学官与否为断,是则知表而仍不知其里。……论事而不知其本,则为已得门径而未臻堂室,刘、宋不足以言成熟之今文学。(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蒙默编:《经学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94页) 刘、宋二人尚且不足以言成熟之今文学,况夫龚自珍、魏源辈乎?“故龚、魏之学别为一派,别为伪今文学,去道已远。激其流者,皆依傍自附者之所为,固无齿于今古文之事。”(同前,95页) 直到廖平撰写《今古学考》,以《王制》《周官》平分今、古二学,明乎辨别今、古文经的标准不在学官,而在礼制,困扰学界的千古难题遂迎刃而解。“推阐至是,然后今古立说异同之所在乃以大明。以言两汉家学,若振裘之挈领,划若江河,皎若日星。”(同前,95页)此功此绩,三百年来惟一人耳!该书大可与顾炎武《音学五书》、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鼎足而立,并列清代经学的三大发明,“于是廖氏之学,自为一宗,立异前哲,岸然以独树而自雄也”(蒙文通:《议蜀学》,《经学抉原》,48页)。 谈论至此,人们想必起疑,蒙文通会不会把乃师说得过于高大?他这番对廖氏的谀辞有几分可信度呢? 然而容易为人忽略,正是这三篇颂扬廖平功绩的论文,竟隐藏了蒙氏的委婉批评: 夫今古学,两汉之事也,不明今古则不足以知两汉之学,然而两汉之事固不足持之以语先秦。推两汉学之本,更溯源于先秦则可,墨守汉人之学以囿先秦则不可。廖师以渊微卓绝之识,博厚深宏之学,既已辨析两汉之学也,而上溯其源若犹未合,此固廖师之欲罢不能者。(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经学抉原》,108页) 廖平《今古学考》订古、今二学分别为孔子早、晚年之学。孔子早年游历燕赵,燕赵之学遂为古学,晚年退而居鲁,鲁学遂为今学,齐地处晋、鲁之间,齐学遂杂糅今、古。蒙文通早年的《古史甄微》就发扬师说:把鲁学上溯至伏羲东方海岱文明,善思辨,主哲学;把晋学上溯至黄帝北方河洛文明,善谋略,主史学;又别立炎帝南方江汉文明,善袄祥,主宗教。蒙氏乃因此说成名于学林。吊诡的是,当1933年《古史甄微》单行本出版时,蒙氏竟已扬弃了它的基本思路。 他在上述引文中称,“不明今古则不足以知两汉之学,然而两汉之事固不足持之以语先秦”。明白指出,廖平把今古文问题一推至先秦是错误的;自己早年把今古文学上溯到伏羲、黄帝,更是错误的。此时的蒙文通已经意识到,从两汉到先秦,隔着一个“周秦之变”,“周秦之变”才是他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 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察觉,当蒙文通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中国处在什么样的历史境况之中。1933年初,日寇大举进犯长城,3月4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十天之内,承德沦陷,华北形势危如累卵!就在热河省陷落之际,蒙氏正好路过苏州拜访章太炎,二人“昕夕论对,将十余日,每至废寝忘食,几于无所不言,亦言无不罄”。据陶元甘回忆: 一九三三年时,大师(指欧阳竟无)看见日本步步进逼,忿慨万端,又想不出有效的办法,就派蒙老师去问章太炎先生有无良谋?手无一兵一卒的太炎先生也只能感慨万端!三位学人虽无办法,但沸腾的热血究不同于卖国求荣者的凉血!(蒙老师有一段笔记,言及此事,给我看过)。(陶元甘:《蒙文通老师的美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盐亭县委员会编:《盐亭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93年2月,61-62页) 除了政治以外,经学当然是二人讨论的重点。蒙氏请教太炎先生:“六经之道同源,何以末流复有今、古之悬别?”太炎的反应是:“默然久之,乃曰:今、古皆汉代之学,吾辈所应究者,则先秦之学也。”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在蒙氏看来,章氏之论不啻于暗示他:两汉归两汉,先秦归先秦,明乎周秦之变,方可言汉学之由来。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近代列强入寇,民族存亡悬于一线,能不是又一次周秦之变?于是上古旧史便与近代国变紧密相连,须臾不离。没有周秦之变,就不会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儒家;没有近代民族危机和共和肇兴,儒家君臣父子之伦就仍然还是中国的官方教义。身处第二次历史巨变中的蒙文通会如何思考两次巨变之间的内在关联? 可以肯定,蒙氏对廖平的评说,不只要吹捧其师,更要从廖平“以礼制分今古”处把握中国历史古今之变的内部机理。用他的话说,廖氏学术的关轴就在于“历史之三代”与“理想之三代”的分离。 二 1919年,对德意志民族而言,同样是危急存亡之秋。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的阴郁氛围中,发表了题为“以学术为业”的著名演讲。韦伯提醒德国青年,不要被新浪漫主义的种种迷狂所惑,不要以为自己掌握了诸如自由民主或共产主义之类的终极真理就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现代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他说道: 人们试图利用严密的自然科学,因为这些学问可以用物理的方法来把握上帝的作品,以此找出一些线索去了解上帝对于这个世界的意图。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除了那些老稚童(在自然科学界当然也可以找到这类人物),今天还有谁会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能教给我们一些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呢?即便有这样的意义,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这种意义的线索?姑不论其他,自然科学家总是倾向于从根底上窒息这样的信念,即相信存在着世界的“意义”这种东西。自然科学是非宗教的,现在谁也不会从内心深处对此表示怀疑,无论他是否乐意承认这一点。([德]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33页) 韦伯直言不讳:古代人和中世纪人都会把真、善、美视作为一个整体,求真的同时就是求善、求美;然而到了近代,理性与信仰却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了。真的东西未必善,更不见得美,它可能丑陋肮脏、无耻下流。现代科学理性不会再像中世纪那样,为了证明上帝的伟大而存在,它会反过来为信仰“祛魅”,使世界走向合理化。此即韦伯所说的,“自然科学家总是倾向于从根底上窒息这样的信念,即相信存在着世界的‘意义’这种东西”。 大抵对现代性问题有所研究的学者,都不敢无视海德格尔的重要判断:现代科学的实质是以种种对意识或经验确定性的追求,遮蔽了对存在本身的追问。诚如刘小枫的近著《海德格尔与中国》所论,海氏对存在与自然的理解远不能说是古人的,它倒毋宁体现了日耳曼文化传统中的“历史处境”或曰“势”。不过我们同样无法否认,海德格尔所说的“种种对意识或经验确定性的追求”,一语道破了现代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思维的实质。 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往往会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自然的秩序或曰“天道”。人间政治就是对自然秩序的模仿,越接近自然秩序的政治统治,就越是好的统治。自然始终都是人的技艺追求的目的,都是人必须投身其中的真实存在。然而近代主体主义却把自然变成了人意识的对象和供人技艺操作的质料。那么对后者而言,还会有什么秩序和德性是永恒的呢? 这种变化起于何时?我们不难在西方历史中确定它的位置:中世纪晚期的唯名论哲学和宗教改革。它们打击了经院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把实体彻底排除出了人类知识的范畴,使永恒存在从此不再是人类知识的对象,而只是单纯信仰的对象。这种信仰不再需要教会或其它公共机构的中介,它完全从属于私人空间。 西方历史固如是乎,中国呢?中国会不会也经历了类似于韦伯所说的“整全性思想的沦丧”“理性与信仰的分离”,会不会也经历了类似于海德格尔和列奥·施特劳斯所说的“自然与技艺的倒置”? 大凡我国的传统学者都会肯定,周公与孔子的区别在于,前者“有德有位”,后者“有德无位”。周秦之变的根本即在于从“德位一致”沦落至“德位分离”。是故三代以上圣人之道行于天地,百姓日用而不知;三代以下圣人之道隐没不彰,学者遂著书立说,载之文字,传于后世。 然而,廖平变周孔“德位之别”为“制度之别”。古学传“三代旧制”,今学传“孔子新制”,前者不过一朝一代的盛世,后者才是万事太平之道。对乾嘉学者而言,三代之治无疑能够垂范于后世,把上古典章考据得越清楚,就越能为后人树法立规。廖平的所作所为则不啻于像后来韦伯那样告诉世人,不要以为研究古史就能立法后世,“古史研究不涉及终极关怀”。美轮美奂的三代之治只存在于儒家理想,远不是过去的真实。过去的真实很可能尔虞我诈、鲜血淋漓。 由是,“历史之三代”与“理想之三代”分裂了。换句话说,经与史、“尊德性”与“道问学”分裂了。 孔子曾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焉。”古代中国人固然不会像古希腊哲人那样绕过历史现象,直接求诸理念、实体,但这并不代表古代中国人没有古希腊哲人那种对世界整体性的思考。此诚如刘家和先生所言,古希腊人善于越过变动的现象追求永恒的存在,中国古人则习惯于在变动的现象之中发现永恒的存在(大意)。整全性思想在中国处,便体现为六经的整体性,体现为有某种一以贯之的圣人之道连接起上古三代的历史事迹。 乾嘉学者治经仍以此六经的整体性为基本准则,仍凭“以经证经”为不二法门。这使得他们总试图于弥缝《周礼》与《王制》之间的制度差异。自从廖平撰写《今古学考》开始,学者索性彻底割裂了二者。晚清今文学家批判郑玄混注今、古文经,但其结果并没有真正回到西汉十四博士“专守一经一传”的状态中去。他们只是拆掉了六经的整体性,把它们还原为“五部不相干的书(《乐》本无经)”(钱玄同语)。疑古派如此,释古派亦复如是。所谓“二重证据法”使得地下古物、域外人类学观念与上古文献互证的效力,大大高于六经文献之间互证的效力,这本身就是拆解六经整体性,就是现代历史主义在中国的表现方式。 念及于此,我们还会笑话蒙文通过分拔高了廖平吗?不妨听听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的判词: 康氏昌言孔子改制讬古;廖氏发明今古文之别,在于其所说之制度;此则为经学上之两大发明。有康氏之说,而后古胜于今之观念全破,考究古事,乃一无障碍。有廖氏之说,而后今古文之分野,得以判然分明。(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663-664页) 三 《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的正标题,正意在于思考上述近代中国学人心智的巨大变革。其中上篇“晚清蜀学与经今文学的另一谱系”,就试图通过廖平的《今古学考》揭示这种思想变革,这当然是仍想“复三代之旧”的常州学派未尝梦见的。 思想革命的另一面是政治革命。历史的巧合往往令人回味无穷,廖平能在《皇清经解》无一部蜀人著作的情况下发动经学革命,似乎暗示了后人四川人能在风气远不如东南沿海开化的情况下,走在辛亥鼎革的前列。中篇“中等社会的革命”就意在揭示这场革命的实相,及其与蜀学认同的关联。二十世纪的大半部分时间里,中国都是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度过的。从阶段论的角度看,后一场革命当然接续了前一场革命。但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从类型论的角度品评一番,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辛亥革命这样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同一类型吗?清政府因保路运动引发的革命浪潮而垮台,然而四川人的“铁路梦”却直到1952年成渝铁路全线贯通,才得以实现。相信这一基本事实已经给出了答案。 值得一提,保路运动可能是四川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动员,廖平当然不能置身事外。他不惟积极鼓吹“破约保路”,更在光复之初成为了四川军政府的枢密院院长。政治立场的不同为廖平的今文学涂抹上了一层与康有为十分不同的底色。还在鼎革之初的1913年,廖平就驰书康有为,规劝其正视革命现实,早日弃暗投明回到人民的怀抱: 西人革命,自图生存,为世界进化必经之阶级。吾国数千年前汤武革命,何尝不如此。(廖平:《再与康长素书》,《廖平全集》第11册,836-837页) 这番话不禁令人想起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按理说左派应该激进地拒斥现状,右派应该保守地维护现状,但在当下的中国思想界,情况却反转了过来。左翼不过在痛斥传统糟粕沉渣泛起,搅乱了社会公平正义;右翼却激进到连革命这一现代中国的合法性根基都不要了。我们的“保守主义者”一面鼓吹哈耶克,一面宣扬“告别革命”,这不像极了叶利钦一面搞“休克疗法”,一面为沙皇平反? 甚或有某些“政治儒家”将拒斥革命、谋求复辟的康有为引为保守主义的同道,殊不觉康氏一贯主张欧美、日本近于孔子的大同之道,当为华夏,中国反而近于夷狄。后来投靠汪伪政权的公羊学家陈柱,不就是这一学说的信奉者吗? 造成上述吊诡现象的根源,端在于革命业已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这种断裂不是事实的断裂,而是法理的断裂。我们诚然可以举出一大堆史实,证明革命后与革命前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谁都无法否认,革命的法理对象就是传统,革命之所以正当,乃是预设了传统不能自发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一个理想的民族国家自然既需要传统,也需要现代。当传统与现代不得不相互对立、互相否定时,百年共和之路就遗留下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 还是廖平,他不惟首先划出了中国人的伤口,更很快开出了医治伤口的药方。廖平指出,近代革命不只是西方人的舶来品,它更是中国人的传统精神,革命不是告别传统,而是回归传统。时过境迁三十几载,蒙文通在“抗战建国”的历史背景下,将恩师的学说发展成了系统的“素王革命论”,彻底跟康有为、陈柱的“素王改制论”划清了界线。 《古今之变》下篇“‘诸子合流’与‘素王改制’”,就是对这一理论的系统评述。不同于廖平“千溪百壑皆欲纳之孔氏”,在蒙文通那里,从孔子到汉儒,隔着一个周秦之变。“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孔孟主张的“汤武革命”是诸侯革命、贵戚革命,陈涉、刘邦实践的革命却是平民革命、群众革命。由谘议局领导的“中等社会革命”和由布尔什维克政党领导的“下等社会革命”不正是这两种不同类型的革命吗? 法家“明君权,削世卿”,打破了“贵贱悬绝”的先秦血缘等级社会,却造成了“贫富悬殊”“皇权专横”的新问题。汉儒不想倒退回先秦去,就必须吸收法家的成果“讥世卿,杜门阀”;汉儒要解决法家的问题,就必须吸收墨家的成果“均贫富,选天子”。总之,汉儒不再是先秦“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旧儒家,而是总结周秦之变并吸收百家之长的新儒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文学研究倒毋宁是一个从先秦到西汉的思想史、社会史研究。蒙文通十分清楚,经历了启蒙的智识人不会再去相信那有如上帝一般的孔圣人了,康有为主张的孔教终不过自说自话。(有朋友可能会质疑,今天的社会业已经历启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仍然大彰其道吗?北美的保皇会确实处处模仿美国新教的宗教仪式、组织方式。但须知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救赎性宗教,就算我们翻遍六经七纬,何曾找得到关于“得不得救”的只言片语?儒家思想在于政教礼俗,拿它去比附救赎性宗教,终归凿枘不投。)在现代社会,任何经学大义都必须在现代历史学研究面前说明自己的合理性。蒙氏的上述努力,无疑反映了我们今天学人不得不面对的境况和症候。 本文节选自《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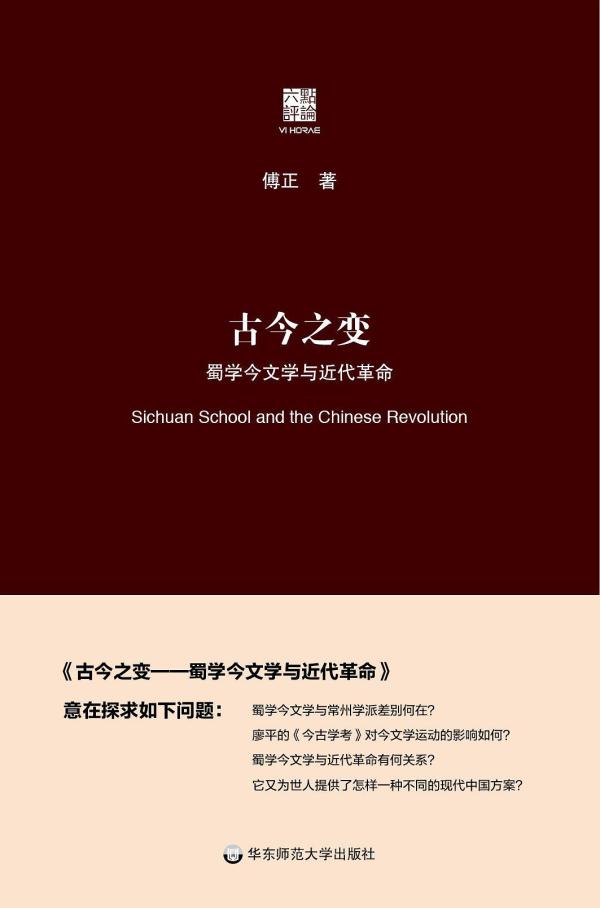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