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赵振铎 辞书学  赵振铎,1928年生,四川成都人,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辞书学家。195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1953年至1955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1959年至1961年,被派往苏联,讲学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莫斯科大学;1975年至1990年主持《汉语大字典》编纂,任常务副主编兼编纂处副主任;2001年,整理的赵幼文遗稿《三国志校笺》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一等奖;2006年获首届“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2012年,担任《汉语大词典》(修订本)副主编;2013年,《集韵校本》获“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二等奖;2014年获“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 “剑南山水尽清晖”“大城少城柳已青”。走进宽窄巷子,漫步少城,可以感受到成都独具一格的西蜀人文风韵。少城,位于蓉城核心位置的历史文化街区,可以说是最原汁原味的“老成都”。在清代成都将军府旧址对面,与热闹的宽窄巷子相隔不远的将军街,则是一条环境清幽的小胡同,胡同里40号曾住着蜀中有名的学术世家赵氏家族,将军街口的历史地名牌也对此专门作了介绍。1928年12月,著名语言学家赵振铎就出生于少城这个书香门第。 赵振铎一生从事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与传承,古今兼修,博精并擅,在文字、音韵、训诂、汉语史、辞书学等领域成就卓著。他采铜于山,综理论说,先后撰述了《古代文献知识》《古代辞书史话》《训诂学纲要》《训诂学史略》《音韵学纲要》《辞书学纲要》《中国语言学史》《字典论》《集韵研究》《集韵校本》等学术著作,及相关研究论文近200篇。大论是弘,导来学以途,可说是中国语言学传承的时代担当。 家学师承 古今兼修 “若问此间奇绝处,但道胸中有丘壑。”赵振铎的求学和治学之路,在那个时代有一定特殊性,家学渊源,打牢传统“小学”根底,转益多师,充分受到现代学术训练,从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的深厚学养中终成一代语言学大家。 自汉代学者林闾翁孺、扬雄以来,蜀中就有独到的语言学传统。近代以来,蜀中语言学家更是人才辈出。有一次拜访赵振铎先生,他曾翻开书架上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第四卷)》,将其中祖父赵少咸的名字向笔者指出,相隔不远就是赵振铎的名字,而他姑父殷孟伦的名字也入选该书。要了解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学术史,中国语言学会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是必读之书,以人物为经、学术为纬,总结了百余年来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历程,而一个家庭入选三位著名的语言学家,这是不多见的。 蜀中赵氏是学术世家,也是有名的教育世家。教育部2021年公布全国首批100个教育世家名单,在家庭和学校树立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赵振铎家庭荣获百家之一,一家四代人,9位教师,心系教育,以学传家,为国育才,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赵振铎的祖父赵少咸(1884—1966)是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曾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在学术思想上赓继乾嘉学派戴震、段玉裁、王氏父子等大师,与章太炎、黄侃等多有交游,著述十余种,其学术巨著《广韵疏证》《经典释文集说附笺》声名远播,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如李一氓、徐仁甫、郭君恕、刘君惠、周法高、殷焕先、钟树梁、李孝定、王利器等,皆出其门下。程千帆曾赞叹其人其学:“自乾嘉以来三百年中为斯学者,既精且专,先生一人而已。”赵振铎的父亲赵幼文(1906—1993)是我国老一辈历史学家,治魏晋南北朝史,一生从事“三国”研究,著有《曹植集校注》《三国志校笺》等,先后任教于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后因熟稔三国魏晋史料,被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调入历史研究所工作。幼年时,赵振铎从父亲赵幼文读《三字经》,用的就是章太炎的重订本《三字经》。赵振铎的姑父殷孟伦(1908—1988)曾任四川大学、山东大学教授,早年受业于黄侃,并得章太炎的指导,在中国传统语言学各个方面具有广博深厚的基础,又于1935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接触了西方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可以说,从祖父、父亲和姑父等著名学人身上,赵振铎的求学和治学在多个方面受到章黄学派的深刻影响。 中国传统学术的“小学”涉及文字、音韵、训诂,是古代治学的基础学问。赵振铎从小受家学熏陶,练就了传统语言学的“童子功”。祖父是赵振铎的“第一个老师”,对他的影响最为深刻。小学开始,祖父便教他读《诗经》《左传》,每天早晨需将当天讲解的内容背诵后才能去学校,初中读《礼记》,高中学《说文解字段注》,祖父严格要求,段玉裁书中所讲词义、名物典章制度等都要一一学习,每天读五个字,三年读完。1948年,赵振铎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祖父又指导他读音韵学,课后标点《广韵》,要求注意清音、浊音,并用不同颜色笔批注。1952年,赵振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祖父又指导他标点《经典释文》,研读《广韵疏证》。正是因为家风学风严谨,赵振铎打下了坚实的传统语言学基础,文字、音韵、训诂皆通。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留校后的赵振铎,被分配到四川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字组教学,担任甄尚灵教授的助教,由此开始接触现代语言学。甄尚灵1951年从耶鲁大学回国,主要研究现代语言学理论,授“语言学引论”“中国语言学”等课程。赵振铎在助教工作中,深感许多理论从未听过,自觉还没踏进现代语言学的门。为了学好语言学理论课程,他突击学习俄语,一个多月后便借助字典读书,又花了半年时间通读苏联学者契科巴瓦所著《语言学概论》,外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53年,北京大学开设语言学教师进修班,接收全国各地的7位教师进修语言学,赵振铎就在其中,另外还有武汉大学李格非、南开大学陈坚、云南大学吴进仁、西北大学杨春霖、兰州大学顾正、吉林大学许绍早,这些人后来在中国语言学界都颇有成就。 在燕园,赵振铎师从高名凯(1911—1965)先生学习语言学理论。在这期间,他又问学于魏建功、袁家骅、周祖谟、李荣、王力、岑麒祥等先生。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相关课程,如周祖谟的“语言词汇”课、魏建功的“语法”课、王力的“汉语史”、岑麒祥的“普通语言学”等,赵振铎都充分吸收。在他看来,“北大的两年是很关键的一个时期,因为以前学到的是传统语言学的方法;北大以后,学到了现代的语言学方法。学得比较吃力,但是收获很大,帮助我把现代语言学的理论运用到传统语言学方面”。 1955年,北京大学进修结束,赵振铎回到四川大学,担任“语言学引论”“现代汉语”等课程教师。1959—1961年,他被派往苏联讲学,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莫斯科大学讲授“现代汉语”“中国文化概论”“汉语简论”等课程。在苏联的两年,赵振铎充分利用获得学术资料的便利,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语言学理论,除了教学,他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列宁图书馆(现为俄罗斯国立图书馆),遍览当时不易读到的学术书籍和资料。在苏联讲学期间,赵振铎在图书馆记下了几十本笔记,大大开拓了学术眼界。现代语言学眼界与传统语言学根基的有机结合,为赵振铎的学术人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主持“两大” 编研共进 赵振铎学术生涯用力最为精深之处当属辞书学,从事辞书事业四十余年,主持“两大”(《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成就显著。同时,作为《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两部巨著的副主编,全国学者只有赵振铎一人。此外,他还参编了《成都大词典》《四川百科全书》等,涵盖字典与词典,普通语文词典与百科词典,小型、中型、大型辞书,或主持其事,或指导后学,均亲力亲为。 中国有悠久的辞书编纂传统,但“大国小辞典”的状况曾长期是中国语言学界的痛点,与泱泱文化大国的地位不相称。1975年5月,“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上确定了160种辞书的编纂规划,这既是国家辞书编纂事业的一个标志性会议,也是赵振铎由语言学研究向语言学研究与辞书编纂、辞书研究相结合转向的起点。 赵振铎对辞书编纂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辞书在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社会需要辞书。”“一个民族,在它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国民教育,语文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辞书则是学习语文的重要工具。辞书还为读者提供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  《汉语大字典》是辞书编纂规划里的重要大型语文字典,确定由湖北、四川两省组织专家协作编写。赵振铎主动请缨,一来字典编写与他自身专业结合,二来辞书可说是一种文化界的“大国重器”,对人民有意义,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字典的编写工作中来。《汉语大字典》湖北方面由李格非主持,四川方面由赵振铎主持,两人为常务副主编。主编最初空缺,1979年11月,教育部下文由徐中舒先生担任主编。汉语大字典编纂处在四川成立,赵振铎又担任编纂处副主任,主持编纂处日常业务工作。《汉语大字典》编纂工作从1975年启动,至1990年付梓,前后长达16年,赵振铎深入编纂一线,查找资料,核对文献,拟定提纲,撰写凡例,往往注意到一般辞书编纂者不太注意的方面。赵振铎强调,辞书编纂中要注意“衍、脱、讹、倒是古籍错落的四种情况”,书籍出错的原因主要有“无心之失”和“有心之误”两种。无心之失,如校书抄书之人水平不高、抄写不慎,刻工疏忽等;有心之误,指书籍整理者因为某种原因篡改原书。《汉语大字典》共收楷书字头5万多,是当今世界上收集汉字单字最多的字典,总字数两千多万,堪称“汉字的档案库”,是继《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之后,国内外规模最大的汉语字典,集历代字书之大成。 2012年,《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编纂工作开始,华建敏同志担任主编,赵振铎与蒋绍愚、张斌共同受邀担任副主编。时年已84岁高龄的他勤勤恳恳投入其中,“征求意见稿”送到他手上后,他一一审读,在书上眉批旁批,朱墨烂然,多能发现其中未安之处,为人为文皆严谨如斯。目前,《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的编纂工作仍在继续,新增内容将达20%,预计达25册体量,有望2023年完成。 基于《汉语大字典》等辞书编纂实践,赵振铎将辞书编写与科研结合,“编”“研”并进,以“实”践“论”。他的研究领域涉及辞书的方方面面,包括收字收词、古今音读、古文字形体、释义问题、书证举例等,撰写了大量辞书学理论论著,先后出版了《古代辞书史话》《辞书学纲要》《字典论》《辞书学论文集》等著作,以及辞书研究论文80余篇,如《义项琐谈》《审音述闻》《关于偏义复词》《字典杂议》《说讹字》《字源考订与字头编排》《古文字形体的收列和字形解说》等。赵振铎的这些学术工作,为现代辞书学构建了系统的理论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字典编纂成果多、理论少的状况,丰富了汉语语文字词典编纂理论的研究。 赵振铎在辞书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对于中国现代辞书学的学科建设无疑具有奠基与开创之功,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其辞书学学术活动被收入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词典研究中心的报告,该报告收列世界各国重要辞书学家,中国自汉代扬雄以降,仅60余人,赵振铎便名列其中。2006年,赵振铎获得首届“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可说是中国现代辞书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著书立说 博精并擅 《集韵》是宋代继《广韵》后的又一部大型官修韵书,全书收字五万余,字头三万多,音读、义项、字义解释丰富,具有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辞书学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赵振铎认为,校理疏通该书,对于使用这部辞书,继承我国重要文化遗产,都会有极大的好处。 1990年,《汉语大字典》编纂工作结束后,年届62岁的赵振铎准备退休,但被国务院学位评审委员会评为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便又满怀热情投入教学及科研,著书立说。他对《集韵》的专门研究也始于此时。 然而回溯起来,赵振铎对《集韵》产生兴趣发端于1956年,当时我国部署开展“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规划”工作,组织上号召青年人“向科学进军”,他即打算学习祖父赵少咸整理《广韵》的治学路径,对《集韵》进行研究。《集韵》向称难治,材料庞杂,研究难度甚于《广韵》,清代段玉裁、王念孙等学术大师都有心于此,但并未完成,没有几十年的功夫是办不到的。祖父赵少咸建议他多读一些书,有所积淀后再考虑专书研究。 研究《集韵》旧事重提是在1975年,赵振铎与李格非讨论《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工作,认为《集韵》收字众多,若是弄清那些字的来龙去脉,能够大大推进《汉语大字典》的编纂进度。于是,在编纂字典过程中,赵振铎对接触到的《集韵》有关材料都尽量收集、抄录,他利用废弃的大字典工作本,剪贴了两部《集韵》做工作底本,将收集的资料过录在上面,到字典竣工时,他收集的资料已经蔚为可观。  1989年 《汉语大字典》编写研讨工作照 1989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他从中了解到更多《集韵》的版本及研究情况,发现之前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得还不够,决心找机会到全国各地访书以弥补缺憾。 1990年,赵振铎申报的博士点基金项目“集韵校正”获批,经费5000元,他又拿出自己的部分积蓄,与夫人鄢先觉先后去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宁波天一阁文管所、杭州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等访书,查阅了不少善本。 此行对于《集韵》的版本及研究情况有了更多了解,基于此赵振铎提出了研究《集韵》的两个路径:一是总结前人的校勘成果,在此基础上编出可资利用的《集韵》校本,让后来学人利用该书时能有所凭依;二是从前代文献中钩稽出可证明《集韵》书中音义来源的材料,充实其内容,使其更好地发挥工具书作用。这一学术计划,堪称规划庞大,工作艰巨。 赵振铎有条不紊在《集韵》研究上不断精进,厚积薄发,成果不断涌现,给学术界带来不少惊喜。2006年,《集韵研究》由语文出版社出版,该书从辞书学及文献学两个角度全面系统地整理分析《集韵》。2012年,《集韵校本》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顾千里嘉庆十九年(1814)重修曹氏刻本为底本,辅以五种宋本、影宋本和清人三十余种成果作为校雠本,对《集韵》做了全面校理,是学界首次对《集韵》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整理,书中既有校勘的文字、词语的疏通证明,也有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的考证等,是《集韵》研究史上的重要研究实践和历史担当。 目前,94岁的赵振铎依然耕耘在《集韵》研究的路上,正在整理中的《集韵疏证》是《集韵》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集韵研究》《集韵校本》的基础上,做文字形、音、义的疏通证明,现已经完成8卷,文字达300万之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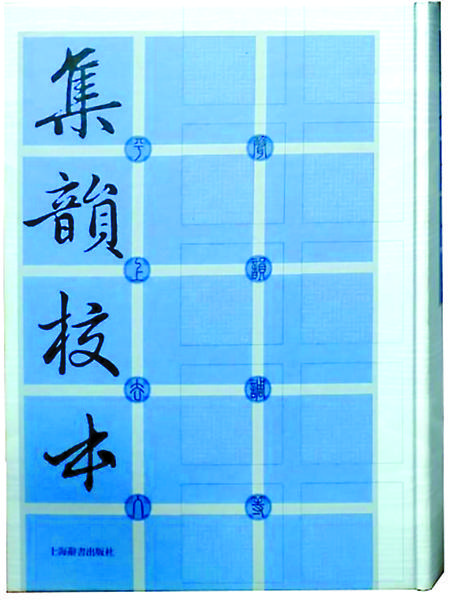 书出众手,则难以备善。为求严谨,赵振铎没要助手,坚持每一个字都亲自录入电脑,每天上午、下午有规律地工作两三个小时。为便于科研,他从1991年63岁时学习操作电脑,此后便一直用电脑工作。赵振铎表示,《集韵疏证》字数众多,不少“怪字”字库里没有,需要做技术处理,录入费时,如进展顺利,有望2022年完成。 2013年,赵振铎凭借《集韵校本》荣获第十五届“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该奖项是中国语言学界最高荣誉,授予对汉语或中国境内其他语言的现状或历史研究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学者。“王力语言学奖”一直秉持“宁缺毋滥”原则,素以学术水准要求高著称,事实上,自1986年“王力语言学奖”设立以来,共评选19届,一等奖经常空缺,至今只颁发了9次一等奖。作为《集韵》研究方面的扛鼎之作,赵振铎《集韵校本》获此殊荣堪称众望所归。同年,该书还荣获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二等奖;2014年又获得“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 所谓“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在赵振铎看来,一个语言学家应该“由约返博”,知识面要广,特别是语言学领域,从文字、音韵、训诂,到传统语言文字、现代语言理论,以及古代地理、古代动植物等领域的知识都需具备,强调治学不可门路狭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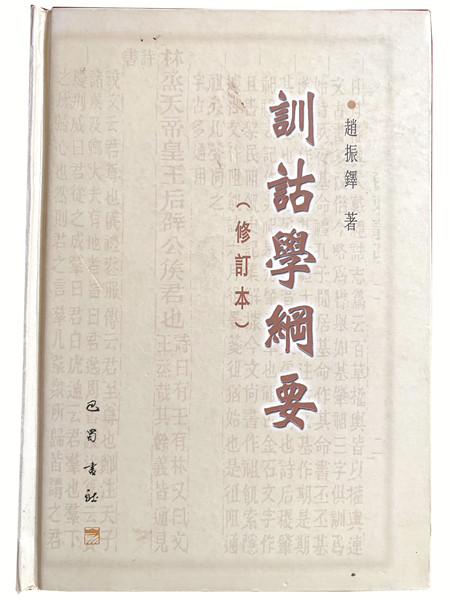 赵振铎深谙于此,在语言学各个方面均有研究涉猎。《古代辞书史话》(1986)、《训诂学史略》(1988)、《中国语言学史》(2000)等是赵振铎历史观念的外显。在语言这个大领域内,他还著有《古代文献知识》(1980)、《训诂学纲要》(1987)、《音韵学纲要》(1990)、《辞书学纲要》(1998)、《骈文精华》(1999)、《字典论》(2001)等,博精并擅、博而不散。正是有了通览语言学史的深厚功力,赵振铎的语言研究达到了“胸中有丘壑”的境界,只有从全局性的博大视角厘清语言要素的历史源流及发展演变,才能真正认清语言的特点。 启导后学 金针度人 《礼记·学记》云:“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1952年,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赵振铎留校任教至今,2022年即整整70年,设帐巴蜀,讲学四方,诲人不倦,可谓桃李满天下。 中国学界素有为前辈大家学术祝寿的人文传统,相关学人精心撰写论文祝寿,结集为学术纪念文集。翻开编委会惠赐的《涛邻雅集:赵振铎先生八八华诞暨从教六十五周年纪念文集》,书中收录文章兼容并蓄,内容小到对一音、一字之辨,大到学术争鸣以及学科发展,包括音韵、文字、训诂、词汇、语法、方言、辞书、文献等,涵盖了汉语文献语言学的方方面面。内容博雅丰赡,反映了他的弟子在文献语言学各领域的耕耘收获,也映现了赵振铎治学包容,涉猎广泛,其中又有共同的学风——推崇言不虚发,做精致讲究的学术。 回顾教学生涯,赵振铎戏称为“三上岗”: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0年,准备退休时被评为博士生导师,开始二次“上岗”招收博士研究生,2000年办理退休;2006年,学院又请年届78岁的他“三上岗”,继续培养博士研究生。赵振铎先后培养了硕士12人、博士14人,访问学者3人,学海摆舟,金针度人,将他们“送到幸福的彼岸”,而今,他们多已成为中国语言文字领域内学有专精、成就斐然的专家学者。 “赵先生是永远用微笑面对一切的先生。他的严格要求,循循善诱,都是在谈笑风生的气氛中完成的。”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汪启明是赵振铎的大弟子,致力于汉语言文字学和古籍整理与出版。汪启明回忆,80年代曾与赵先生在讲座、学术会议等两次见面,当时虽无深交,但赵先生给他留下了学识渊博、随和待人的印象。1991年秋天,他带着一盒茶叶,在川大桃林村赵府,请赵先生正座,然后恭恭敬敬鞠了一躬,便是入了师门,成为赵先生的开门博士生。赵振铎在学术上严格要求,对学生的论文他总是用蓝色笔、红色笔、绿色笔各改一次,细细批过后,才用黑色笔定稿。在生活中的赵振铎,又是宽和的。汪启明说道:“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中,先生总是我们坚实的臂膀。我们有了一点成就,或是出现什么困惑,总要报告先生。先生之恩,山高水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印象就更为强烈。”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1993年初考取赵振铎的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汉语、汉语语法学、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的教学与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先秦汉语助动词研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刘利说:“从开始选题到最后完成初稿,其间每一步都是在赵先生的指引下迈出的。”经赵先生指导,刘利在占有语料上面下了很大功夫,论文引用的材料,上自《尚书》《诗经》、金文,下至《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对每部古书中的用例也都做了详尽的数据统计。此外,他向赵先生学习,积极谨慎地吸收现代语言学分析语言的程序和方法,把语义分布、句型比较以及替换、改写等手法,运用到对上古语言事实的分析中,使助动词的语法、语义功能得以清晰揭示出来。刘利表示,求学阶段跟随赵先生的学术训练,是自己一生学术的基础。 “回顾我这一生,日子还是没有白过,也可以交一份差可的试卷。但愿假我以年,还有春秋,能够把我预定的工作做完。”赵振铎这样说道。 赵振铎七十余年锲而不舍从事学术研究,深深感染了晚辈。他的儿子赵开说,父亲挚爱中国语言学研究,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子女宽厚温情,对学生亦师亦友。家中时常有客人来访,或请教问题或探望问候,父亲都要收拾妥帖,热情接待,在约定时间前一两个小时就要给对方打电话关心“到哪儿了”。他生活规律,按时入睡起床,每天要睡满10个小时,然后开始工作。近来,老先生因病住院,仍然时刻牵挂未完成的《集韵疏证》,希望能早点回到书桌前用他熟练的“一指禅”打字。 “学至乎没而后止也。”赵振铎将学术人生的经验总结为四点以飨后学:第一,与时俱进,知识更新非常重要。第二,教学、科研要紧密结合,两手都要抓。第三,为人、为学要心态平和。第四,健康的身体是一切的基础。赵振铎一丝不苟的研究态度,与时俱进的治学精神,古今兼修的学术眼界,以及博精并擅的学术成果,堪称中国语言学传承的时代担当。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