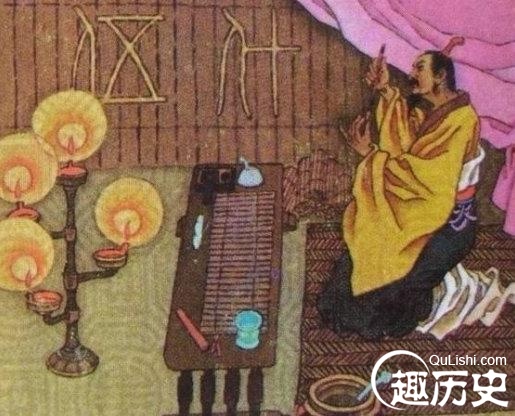|
史学界普遍认为,古代历朝变法失败的原因有三: 1.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强有力支持。 2.变法触动了实力集团的既得利益,引发他们动用一切资源拼死抵制、破坏,比较而言,变法派的势力相对弱小。 3.变法的举措可能因超前而不尽符合实际,或因变法派操之过急,缺乏冷静耐心等。 其实,上述认识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历代变法失败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受制于王朝盛衰的周期律。换言之,当一个王朝衰亡的命运已经铸成的时候,往往并非人力所能改变。 比如,到了王朝中期,君臣远非开国时代可比。想当年艰苦创业,大刀阔斧,皇帝雄才大略,目光远大,臣子艰苦朴素,兢兢业业。而今文恬武嬉,安于享乐,皇帝也没有了祖辈的威风,根本约束不住臣子的腐化堕落,更何况很多皇帝带头腐败,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家政治就更不可收拾了。 同时,和平时间一长,人口肯定越来越多,而国土面积的扩张却是有限的,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吃饭问题、就业问题尖锐地摆在统治者面前。古代的中国是农业社会,经济形态单一,基本无力解决上述问题。而且,随着人口的膨胀,官僚队伍必然扩编,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与民争利,无所不用其极,普通百姓越发没有活路了。种种问题的积累,预示着大动荡的不远,在这种情况下,企图通过体制内的调整,缓和矛盾,扭转危机,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表面上看,变法比革命的代价小,但就难度而言,却远远大于血流成河的革命。因为革命只有一个敌人,大家戮力同心,舍命向前,往往可能死里求生,杀出一条血路。相反,变法是在维护现有体制的前提下,重新调整利益分配的格局,化解矛盾,达成妥协,要处理的关系堪称千头万绪,面临的阻力可想而知,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运用极高的政治斗争艺术,其难度可想而知。 古话说得好:打铁先要自身硬,而中国古代王朝中期的变法家的群体形象却不理想。比如,北宋王安石领导下的变法团队大多由见风使舵的政客、首鼠两端的小人、贪污腐败的官吏构成。当时皇帝倾向变法,变法成为时尚,于是,一些人前来投机。像变法派的第二号人物吕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亲信,据说王安石对他有“父师之义”,但为了争夺宰相的位置,吕惠卿对王安石无情打击,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另一位变法干将邓绾本来靠巴结王安石起家,见状立即墙倒众人推,加入到打击王安石的行列中,不久见王安石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又摇身一变,转而攻击吕惠卿,重投王安石。有人指责邓绾无耻,他居然回应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 至于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奸臣蔡京,也曾是变法派中的先锋干将。 历代变法派往往有一个难以挣脱的“小辫子”——腐败。他们要重振朝纲,而自己的操守却不干净。王安石变法中,变法派里面不乏腐败分子,借变法之机贪赃枉法,搜刮民财,但王安石本人尚属检点。而明代变法的领导者张居正却不能以身作则,他独断专横,生活豪奢,每餐菜品上百,“犹以为无下箸处”,死后被抄家,没收的财物折合白银近二十万两,良田几百万亩。当然,这很可能是家乡亲人、仆人背着他所为,但他主政期间,三个儿子考中进士,而且名次极为理想——一个榜眼、一个状元,这是偶然的巧合吗?天下的读书人会心服口服吗?这些人推行变法,怎能不让人怀疑其私利的成分,又怎能抵挡得住反对势力的反攻? 史学家还抱怨古代的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有力支持。其实,中国古代的皇帝代表着各方面的利益,帝王术的基本原则是“平衡”,而不是“选边站”,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变法一天也坚持不下去;但随着变法的深入,必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皇帝统筹全局,自然要随时调整,要想让皇帝孤注一掷,投身变法,本身就是违背王朝政治规则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如果说王朝中期的变法鲜有成功的话,王朝晚期的变法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危险的举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如果不搞变法,一个衰败的王朝尚可维持时日,一旦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可能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比如元末丞相脱脱急于挽救王朝,搞“旧政更化”,推行与汉文化接轨的变法举措,又在经济上减轻人民的负担,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针对通货膨胀进行的钞法改革导致经济失控,疏浚黄河的最直接结果是千千万万的治河民工在工地竖起了反元大旗,最终脱脱成了元亡的替罪羊,被流放并被毒死。再比如清末统治者急于挽救王朝,居然想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结果激发起了民主化的大潮,最终被埋葬在辛亥革命之中。清亡后,有遗老反省,认为如果不搞政治改革,“虽以无道行之,未遽亡也”。 也就是说,即使推行独裁统治,谁反对就镇压谁,也不会那么快地亡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