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语文学被人文主义者视为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19世纪语文学随着学科专业化成为专门学科,并在德意志地区成为显学。20世纪初傅斯年留德期间曾受到语文学熏陶。在他看来,语文学在形式上与传统考据学相似,但却比考据学更科学。傅斯年回国后,将语文学用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并将其以科学的面貌呈现给世人。本文通过梳理语文学在德国的发展,揭示德国语文学的研究方法如何影响了傅斯年的历史研究,并探讨在科学主义盛行的中国,傅斯年将“科学”视为话语以此推动语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关键词:傅斯年 语文学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科学主义 作者简介:张一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1928年时任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的傅斯年向蔡元培建议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3月在广州中山大学筹备史语所,7月正式成立,这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民国时期所创立的重要学术机构,广为人所知,直至现在,仍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当人们看到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一名称时,很多人将其理解为研究历史与语言的机构,一些论文甚至在英文摘要中直接将其翻译为the History Language Institute。但殊不知,傅斯年曾亲自将其译为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众所周知,语言学的英文应为linguistics,在20世纪linguistics在英美也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傅斯年也曾延聘留学美国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担任史语所研究员。那么为何傅斯年将史语所译为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philology又与历史研究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在展开讨论之前,笔者希望先对philology这一概念进行界定。Philology(德语:Philologie)可译为语文学或语义学、语言学等,它起源于古希腊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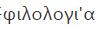 即爱(φιλο)与说( 即爱(φιλο)与说( )的合成词。据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解释,philology一词有三种含义:(1)对学问和文学作品的爱好或文学研究,其中包括对文献的考订解释;(2)与哲学(philosophy)相对,表示对演讲、辩论的爱好;(3)语言学的前身,在英语世界多指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虽然第三层含义出现最晚,在英语文献中首次出现是在1716年,但这一含义成为philology最为通用的意涵。而在德语中,与英语含义相似:(1)一种研究特定语言文本的科学,(2)语言和文学研究。当该词传到东亚时,译名并不统一,日本曾将其翻译为“博言学”,后改为“言语学”。民国初年,傅斯年曾积极推动philology的传播,他将其翻译为“语言学”、“言语学”或“语学”,如历史语言研究所其英文名便是the Institute of Philology and History。而胡适则主张翻译为“文字学”,《新英汉词典》则将其译为“语文学”和“语文文献学”,现在多数学者采用这一译名。 )的合成词。据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解释,philology一词有三种含义:(1)对学问和文学作品的爱好或文学研究,其中包括对文献的考订解释;(2)与哲学(philosophy)相对,表示对演讲、辩论的爱好;(3)语言学的前身,在英语世界多指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虽然第三层含义出现最晚,在英语文献中首次出现是在1716年,但这一含义成为philology最为通用的意涵。而在德语中,与英语含义相似:(1)一种研究特定语言文本的科学,(2)语言和文学研究。当该词传到东亚时,译名并不统一,日本曾将其翻译为“博言学”,后改为“言语学”。民国初年,傅斯年曾积极推动philology的传播,他将其翻译为“语言学”、“言语学”或“语学”,如历史语言研究所其英文名便是the Institute of Philology and History。而胡适则主张翻译为“文字学”,《新英汉词典》则将其译为“语文学”和“语文文献学”,现在多数学者采用这一译名。海内外学界关于傅斯年的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传统观点认为傅斯年深受兰克史学影响。而卞修全则认为傅斯年曲解了兰克史学。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傅斯年与兰克学派的关系,但是却认为傅斯年史学思想来源多元,同时受到新史学思潮影响。90年代许多海外学者开始利用傅斯年档案研究其史学思想,基于对傅斯年阅读史考察,纠正传统观点。王汎森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详细论述了傅斯年史学思想中的欧洲资源,王晴佳在《以史寻国》(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中论证了傅斯年受到欧洲语文学(philology)的影响,并认为傅斯年希望打通语文学与清代考据学,而后王晴佳又在《科学史学乎?“科学古学”乎?》中进一步延伸,分析了傅斯年“近代历史学是史料学”这一观点与德国“古典学”(Altertumswissenschaft)的关系。施耐德(Axel Schneider)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关注傅斯年思想中普遍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12杜正胜指出语文学(philology)在傅斯年思想中的重要性,周梁楷则从语文学与历史学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傅斯年与语文学的关系。 近十几年来,大陆学者也开始关注傅斯年思想中的非史学资源。李泉认为傅斯年在柏林求学时,修习了“比较语言学”等相关课程,希望用语言学解决哲学问题,在此李泉主要将语言学解读为“linguistics”,沈卫荣则在讨论《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指出傅斯年所讲的“语言学”其实是philology,但更多强调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层面。桑兵则指出傅斯年的想法或许来自德国,但其内心典范是法国汉学。虽然许多学者都关注到傅斯年与语文学的关系,但是大多点到为止,并未深究。关于傅斯年与语文学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多,台湾学者张谷铭基于对傅斯年和赵元任的研究,分析了philology与linguistics在中国的传播,并讨论了傅斯年心目中的语言研究,与在德国所受语文学训练的关系。在其近作《Philology与史语所》中,张谷铭进一步阐述其观点,并分析了后来philology在中国衰落的原因。 不容否认,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傅斯年与德国语文学的关系,但是大多是从中西史学交流的角度去分析,对于傅斯年提倡philology的原因,也多是从考据学背景去考察,鲜有人提及傅斯年的思想与当时科学崇拜的关系,本文基于近代中国科学崇拜思潮分析傅斯年吸收语文学的原因,并分析傅斯年如何运用科学的话语宣扬自己的主张。 一、德国语文学对傅斯年的影响 一般认为,近代中国史学存在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两大潮流,而傅斯年因“近代史学便是史料学”被视为“史料学派”的代表,甚至被誉为“中国的兰克”。但据王汎森研究,傅斯年早年并未读过兰克的相关著作,而且若仔细比较兰克与傅斯年的思想,则会发现两者存在一些差异。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通常被视为“客观史学之父”,但是如果单从考订史料来说,兰克并不比前代学者更高明,德国学者斯蒂凡·约尔丹(Stefan Jordan)曾指出,19世纪中期,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发展出完善的考订史料的方法,并认为历史研究只需研究史料,展现所有细节即可。兰克则不同,一方面,兰克极为重视档案,在《近代史家批判》中,兰克在批判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的《意大利史》时指出,圭恰迪尼并未使用档案,而是大量采用他人的记载。另一方面,兰克又极为关注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在《论普遍历史》中,兰克区分了“Historie”与“Geschichte”两词的意涵,兰克认为:“历史(Geschichte)这个词更多强调客体性,而史学(Historie)则与主体性的关系更为密切;前者主张科学的事实性,后者则是科学自身对对象的把握”。这两点看似矛盾,其实反映的正是兰克那句“历史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名言的真谛,一方面,兰克需要用系统化的方法考订史料,而另一方面则需要将这些档案史料相勾连(Zusammenhang)构成一种历史叙述,通过叙述表达史家观点。因此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Iggers)曾这样理解兰克,“兰克所理解的严谨的学术性,是预先设定了严格禁绝一切价值判断的。正如他在为他博得了应聘柏林大学的那一部论意大利战争一书中有名的序言中所说的,历史学家应该避免‘评判过去’而把自己仅限于‘表明事情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然而同时他又摒弃了任何一种要把确定史实当做历史学家根本大事的实证主义。” 然而我们再反观傅斯年,傅斯年早年留学欧洲,后回国创立史语所,主持殷墟发掘、城子崖发掘等多项考古工程,并且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称《旨趣》)中明确宣称反对疏通,只要把材料整理好,事实自然明了,处理材料,应秉持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态度。这与兰克本人的史学思想大相径庭,兰克强调使用档案,并未在其著作中采用多少考古材料,而傅斯年则主张使用考古材料,反对疏通。那么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更多受谁影响? 傅斯年早年为追求“真学问”、解决“大问题”留学英国,学习心理学并旁听了如化学、物理等理科课程。他在1920年给胡适的信中写到:“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大学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此后学习心理学大约偏重于Biological一派与讲Freudian Psychoanalysis之一派。下学年所习科目半在理科,半在医科。斯年近中对于求学之计划比前所定又稍有变更。总之,年限增长,范围缩小。哲学诸科概不曾选习。我想若不于自然或社会科学有一两种知道个大略,有些小根基,先去学哲学定无着落。”由此不仅可以看出他对这些理科的兴趣,而且还可以看出傅斯年希望通过科学知识认识世界。正如王汎森总结的:“(傅斯年)在伦敦大学的这些年,他的主要目标是一方面摒弃代表中国思维方式的模棱两可、过于笼统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同时运用一些实验的、观察的和数理分析的方法探求人类思想的深层。”傅斯年在伦敦逗留三年,但并未能获得学位,后转而留学德国。留德期间,他受陈寅恪影响,开始关注德国语文学和印度学研究,并修习和阅读了一些语文学的相关课程和书目,跟着陈寅恪参加弗兰克(Herman Franke)的课程。在傅斯年1925年给罗家伦的信中提到“书是买了一部藏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的语学(非其字典),上二件是上课,下一则是写书用。”在这里傅斯年提到的语学,便是德国的语文学(Philologie)。虽然傅斯年对语文学抱有极大兴趣,而且主张基于语文学建立中国的古典学,如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顾颉刚的《古史辨》吸收了明清考据学的优秀成果,若能引入近代考古学的方法,则可以建立中国的“古典学”(Altertumswissenschaft),而且傅斯年还提到应用梵语来研究佛学,“弄佛学则大纲是一个可以应用的梵文知识,汉学中的章句批评学无所用之。”但是从傅斯年的学籍档案可以看出傅斯年当时梵语课程并未取得成绩,傅斯年回国后也多涉猎中国古代史领域,并未采用梵语和中亚文献进行研究。傅斯年更多吸收了语文学的方法和理念,并希望运用这种西方语文学方法和理念重新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傅斯年曾购入《古典学导论》(Einleitungindie Altertumswissenschaft)一书,现藏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傅斯年纪念室,如果我们对照《古典学导论》中的相关内容,则会发现傅斯年深受《古典学导论》的影响。《古典学导论》首先讲述了古典学研究的方法论和历史,之后分别论述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学、语言、诗学、私人生活、钱币学、艺术、宗教、科学、哲学、政治结构等方方面面。其中在方法论部分,又从语文学-历史学的方法,物的语文学,考古学方法等方面进行论述。 傅斯年曾在不同地方多次强调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认为“思想就是语言”“思想以语言为体,而不只是外用”,在《战国子家绪论》中傅斯年提到:“今试读汉语翻译之佛典,自求会悟,有些语句简直莫名其妙,然而一旦做些梵文的功夫,可以化艰深为平易,化牵强为自然,岂不是那样的思想很受那样的语言支配吗?”。这一观点与《古典学导论》中所提到的“语言是思想唯一的表达方式”极为相似。1928年傅斯年曾在给胡适的信中写到:“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业已筹备,决非先生戏谓狡兔二窟,实斯年等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黽勉匍匐以赴之。”由此可以看出史语所寄托了傅斯年的理想。1927年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中提出:“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端甚早,中国所有的学问比较成绩最丰富的也应推这两样,但为历史上种种势力所缚,经历了二千余年还不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学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而在《旨趣》中,傅斯年更为系统的阐述了语文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文章一开头,就提到“近代的历史科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史学方法之大成。”如张谷铭分析《旨趣》开端时便指出,“傅心目中的历史和姚从吾相同,还是以搜集考订史料为主,以philology为本的历史学。”而且在《古典学导论》中曾明确提到历史学与语文学的关系,“历史学与语文学是一对近亲姐妹,彼此相互发展:一方的进步依赖与另一方的帮助,一者的匮乏也使另一者止步不前。”傅斯年谈论史料扩充,其实是受到古典学的影响。傅斯年认为“在中国的语言学和历史学当年之有光荣的历史,正因为能开拓的用材料,后来之衰歇,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不添新的了。”而应该多多扩充材料,比如傅斯年主张应关注神祗崇拜,歌谣,民俗,各地各时雕刻纹饰差别,这些其实都是德国古典学所关心的内容,如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等人便采用大量民谣研究古典时代。在《古典学导论》中也专门有篇章讲述考古学的方法,实物史料如何佐证传世文献。 傅斯年不仅积极倡导语文学,而且将语文学的理念与方法运用到实践之中,其中《性命古训辩证》便是傅斯年“用语言学方法解释一个思想史问题”的经典之作。傅斯年本人对该书也颇为得意,在1947年中研院院士选举中,傅斯年作为候选人提交的代表作便是《性命古训辩证》与《夷夏东西说》,他在简介中说:“《性命古训辩证》。此书虽小题而牵连甚多。其上卷统计先秦西汉一切有关性命之字义,其结论见第十章。本章中提出一主要之问题,即汉字在上古可能随语法而异其音读也。以语言学之立点,解决哲学史之问题,是本卷之特点,在中国尚为初创。其中泛论儒、墨诸家之言性与天道,引起不止哲学史上之新问题,富于刺激性。其地理及进化的观点,自为不易之论。” 《性命古训辩证》目的是要“用语学的观点识性命诸字之源,用历史的观点疏性论历来之变。”他承接了阮元《性命古训》的观点,认为“性”“命”包含着世俗内涵。与阮元不同之处在于,傅斯年采用“语学”的方法分析性命二字的词源。阮元主要基于传统儒家经典,如《尚书》、《孟子》等进行分析,而傅斯年则搜罗大量周代金文,加以统计、分析。据张谷铭考察,中国当时虽然已经有了甲骨文、金文的搜集,主要是辑古的性质,最多是释读。但是像欧洲语文学一样,全面搜集碑刻金文做字词解读,傅斯年可能是第一人。这种将碑刻铭文用作研究对象的方法,正是德国“物的语文学”(Sachphilologie)的方法,即将语文学的方法扩展到实物研究,如尼布尔便采用了当时的铭文、钱币研究罗马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