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关于章丘城子崖遗址 1930年11月7日至12月7日,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合组的“山东古迹研究会”,以此名义,由李济带队对历城县(今属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进行首次发掘;1931年10月9日至30日,由梁思永带队进行再度发掘(15)。两次参加发掘的人员有李济、董作宾、郭宝钧、吴金鼎、李光宇、王湘、梁思永、刘屿霞、刘锡增、张善等。1930年发掘开10米×1米探沟44个,面积440平方米,1931年发掘45个坑,发掘面积15208平方米(16)。发掘获得大批陶、石、骨、角、蚌、金属器等遗物,其中陶器主要有鬶、鼎、鬲、甗、瓮、罐、壶、杯、豆、簋、纺轮、弹丸、陶文等,石器主要有斧、刀、镞、锛、凿、铲、锤、砺石等,骨角器有卜骨、镞、凿、锥、针、梭、鱼叉、簪等,蚌器有刀、锯、镞、环等,金属器仅有铜刀。遗迹发现有城墙和陶窑。 关于城子崖遗址发掘的缘由,李济认为(17):一个是要选择一处早于夏商周三代的只出石器不出铜器的遗址发掘,以期一步一步追寻中国早期文化的递嬗痕迹;一个是要在中国内地东北大平原上发掘一处区别于分布在中国西部与北部的以彩陶为特征的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为商文化寻找到正真的原始,用以回答复苏且日盛的中国文化西来说(18)。 关于城子崖遗址的年代,报告将其文化堆积分为下层黑陶文化和上层灰陶文化两个时期的堆积,但是没有对两个时期堆积的年代作出具体的推断。李济在《发掘龙山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绩》中认为,“这上层的文化代表我们所知的商末与周初的文化,发现的铜镞与殷墟出土的极相似”,“完全石器的文化,在这一层下:出的陶器,有很贵重的黑色陶器,同时也有少数红色及白色的。石器的种类,有斧、锛、镞、刀、铲等。骨器的种类,有锥、针、簪等。陶器的种类,有鬲、鼎、斝等”。 城子崖的发掘使人们认识到,在彩色的仰韶文化和灰色的小屯文化之外,还存在一个黑色的龙山文化,而三者的年代关系的确认却是1931年梁思永发掘河南安阳后冈遗址解决的,即龙山文化早于小屯殷文化,晚于仰韶文化。 关于城子崖遗址发掘的意义可作如下归纳: 就发掘工作本身而言,城子崖遗址是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中国学术机构主持、采用近代考古学方法发掘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遗址。在发掘中,李济延续了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统一布方方法,以遗址西南角为坐标点,东西向为X,南北向为Y,水平为Z。1930年发掘主要沿遗址中部的南北纵轴开挖探沟,探沟编号冠以“纵中”;1931年发掘主要在遗址周边开挖探沟,探沟编号冠以“A”“B”“C”“D”。 就发掘方法而言,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在文化堆积单位的划分上,早于1931年安阳后冈遗址发掘,在中国首次采用按土质土色划分文化堆积。 就遗物发现而言,城子崖挖出了以黑色陶器为特征的龙山文化遗存,其俨然区别于彩色陶器为特征的仰韶文化。城子崖发掘的最重要意义就是不负傅斯年、李济的期望,果然有了龙山文化遗存的发现。龙山文化的发现首先使得学界认识到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确实存在着一支“组成周秦时代中国文化之一大分子”的中国固有的原始文化。其次是城子崖出土的卜骨、黑陶豆和白陶鬶等遗物,拉近了以殷墟小屯文化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与史前文化的距离,为中国文化找到了更紧密的源头。再次是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如果说彩色陶器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西方文化因素,而其主要分布在太行山以西及以北地区,并未涉足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华北平原地区,而华北大平原上的以黑色陶器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才与殷、周、秦文化有着更为密切的亲缘关系。 就遗迹发现而言,城子崖发现了城墙遗迹。城墙的使用分属于龙山时代和周代的两个时期,晚期的周代城墙是在龙山时期的城墙基础上的利用改造。城子崖龙山时代城址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史前时期”的城址,其发现要较后来在山东和河南境内大量发现的众多龙山时代城址早约半个世纪(19)。 就报告的编写而言,其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编写出版的速度即便在今天也是不多见的。1930年冬发掘完毕,立即开始编辑报告,1931年8月报告编辑完毕;1932年3月,二次发掘品整理完毕。全部报告同时草成。1934年,出版《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田野考古报告。 继李济、梁思永1930年、1931年发掘之后,城子崖遗址又有过两次发掘。 第一次是1990年和199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于对遗址的保护和研究,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试掘和勘探。由于资料尚未正式公布(20),不明其发掘面积、出土遗物、出土遗迹等详情。 据《中国文物报》之《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报道,本次发掘的最大收获是确认城子崖遗址是一处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三城重叠的遗址,并初步探明各时期城址的面积和筑城方法。“解决有关城子崖城址时代的争论,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另一重要收获是“在遗址中找到了1931年发掘的4条探沟的坑位,并重新挖出了4号探沟(21),证实当年认为是龙山文化的黑陶堆积,应是岳石文化堆积。因此六十年来史学界一直认为的龙山文化城址,实际应该是岳石文化城址,即夏代城址。” 关于本次发掘最大收获即“确认城子崖遗址是一处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三城重叠的遗址”,对此学界曾有人提出质疑(22)。其实,关于城子崖遗址城墙遗迹分属三个时期的认识,倒不一定是1990年发掘者的首次发现和认识。1930年和1931年的发掘者已在《城子崖》报告之《建筑之遗留·城墙·墙基与墙身》中有这样的交代:“墙基不是全部建筑在生土上的,例如西墙在大道切口之处,墙基大部分是筑在含黑陶的土层上的;在纵中44、45坑里墙基的两端也是筑在含黑陶的土层上的。”“墙身之建筑虽然大部分是用生黄土,但也有例外:在C4(插图三)与D7-11(插图二)等坑里,我们发现东墙与南墙(最少在发掘的那一小段)靠里面的一半,在2.5公尺高处,约4.5公尺,是用黄土筑成;靠外面的一半,灰土建成。里外两半的分界很整齐,但不是垂直而是向外倾斜的。在工程方面也有不一致之处;灰土部分之夯层一般的厚度较黄土夯层为薄,各层之厚度也不如黄土的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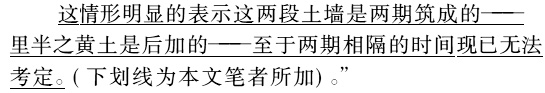 这里所说的靠外的灰土筑成的墙体和靠里的黄土筑成的墙体,显然是指下层黑陶文化时期的两次筑城,而不是下层的黑陶文化时期和上层的灰陶文化时期。因为,在此段文字之后《墙之建筑时期》中,还有这样的文字记述:“当上层灰陶居民住城子崖之时,先一期所筑的土墙虽已坍塌但还有相当的高度(约2-3公尺)可以给与他们多少保障。大概因此他们也没有作大规模的修补。”如果这两次筑城是下层黑陶文化时期的事情,那么,依城子崖遗址还存在龙山文化和周代文化之外的岳石文化的认识,就应该是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两个时期。由于1990年和1991年的发掘材料没有正式报道,我们也还无法将其解剖的城墙剖面与1930年和1931年的城墙剖面作比对研究,也制约了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得出肯定的认识。 城子崖遗址所谓“下层文化”包含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两种遗存的认识,首功应归于20世纪60年代后岳石文化从龙山文化中的逐渐剥离并确认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23)。在《城子崖》报告发表的器物中,城子崖下层出土的陶器大多属于龙山文化,少量属于岳石文化(24)。今天之所以能够在城子崖遗址下层文化堆积中识别出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两个时期的城址,正是因为有了对岳石文化陶器群的认识。 第二次是2013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城子崖遗址再度发掘。由于资料尚未正式公布(25),不明其发掘面积、出土遗物、出土遗迹等详情。据中国文物报《考古圣地结新果》(26)报道,发掘位置选在1930年发掘的纵中探沟。“为保存学术史的珍贵印记,只对探沟东壁进行复刮观察,西壁不动并留下10厘米附土保护。为了贯通整个剖面,还将当时没有开挖的第22~27,40~41两段探沟也挖开,由于探沟南端没有延伸到南城墙,所以将探沟向北延伸了20米,以求能够尽量跨住北城墙。” 本次发掘的主要收获,一是确认遗址中部为万余平方米的低洼地;二是再度证明1990-1991年第二次发掘确认的城子崖城址存在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周代三个时期的堆积,以及每一时期遗存的分布和保存状况。 李济、梁思永主持的城子崖遗址发掘,目前学界还没人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只是傅斯年在《城子崖·序一》中讲到对于上层周代遗存属于“谭墟”的认识,有嫌“过犹不及”(27)。 《城子崖》报告之《附录》是由董作宾执笔的。通过文献的考证认为:谭城在武原河;谭之建国在殷之末叶,谭大夫出现在西周末,谭公出现在卫庄公五年,谭为齐灭在齐桓公二年,谭子再现在战国末,谭城废弃在汉初。对于城子崖遗址上层出土物的年代,董作宾以为,灰陶器类于殷墟(28),齐刀货、铜箭镞为春秋战国。基于文献记载谭国地望、年代与城子崖遗址位置、出土物年代吻合,所以城子崖上层城址应为“谭墟”。2013年“发掘的主要收获一是确认遗址中部为万余平方米的低洼地,不似有大型建筑”。如此,就将上层堆积时期的城子崖遗址说成是“谭墟”,则确如傅斯年所言,还不能定论。其实,从报告的文字中可以读出,傅斯年此处并不是在刻意指出报告的不足,也不是在申明自己不同意董作宾的观点,而是在讲给学人们一种学术理念,那就是“有一分材料,就说一分话”。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