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灾害影响在常熟地方社会中的扩散 常熟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中心位置,在清代隶属于苏州府。雍正二年,“析置昭文县”(29),昭文与常熟同城而治。一般说的常熟地区,包含了昭文和常熟二县。1840年常熟地区的昭文“成灾五分”,常熟“收成歉薄”(30),从受灾分布来讲,“昭邑二百图,有一百八十图成灾,常邑三百图,止一百廿一图成灾。”(31)。本文将常熟当年灾情判定为2级成灾,其受灾程度就整个长江三角洲而言不算特别严重。 1840年水灾中,大量农田被淹,农业成为水灾对社会的直接影响面。六月六日(7月4日)到八日常熟连降大雨,低田、中田已经没入水中:《日记》六月七日记载“王知数自西南乡收麦租回,云低田新秧已没,中田亦渐没矣,若再连阴,恐成大歉,奈何。”(32)六月八日,农田被淹情形加剧:“城外一望汪洋,田与湖接,可扬帆而过,殆与癸未年景不甚相远矣。”(33)再加上海潮溢入,连“地势高仰”的西乡也皆被水,东乡地势较低,“低区圩岸多坍损”,农田被水情形就更为严重,大量的秧苗被淹损。到了10月份,因入秋以来天气转晴,常熟的灾象减轻,但低田仍被水淹没,“惟低区未经涸出者有无禾之叹耳。”(34) 常熟是重要的植棉区,且其棉纺业在长江三角洲占重要地位(35)。水灾影响到的,不仅仅是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种植,还有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生长。棉花需水怕涝,在生长期棉田内水渍和水淹,会造成蕾铃脱落乃至植株死亡,对产量影响十分明显。且棉花虫病与气温、雨日等气象因子相关性较强(36),水灾过后,常熟棉田“未淹处又有虫伤”(37)。这种天气灾害对农业造成的损失是综合性的。 由于大面积的农田受灾,自耕农、佃农等主要以农业为生的群体承受了最直接的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首先的反应自然是尽量补救,减少损失,利用降雨的间歇通过车水的方式进行田间排水,补种秧苗。但降水连绵,“农民方车水出田,补莳稻秧,又前功尽废矣,为之濠叹。”(38)这种补救措施的效果相对有限。 为应对灾害损失,农民最常见的措施是调整消费结构,压缩开支。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压缩农家能自己生产的主食的消费。如1840年水灾使武进芙蓉圩地区圩堤坍塌,田庐被淹,而村民向高地移居,“惟长孙守户,日仅一炊而已”(39)然而,根据黄敬斌对18世纪中期江南农民的消费结构研究,19世纪农家的生活消费的各个项目大体上缺乏弹性(40),压缩的空间并不大。 除了尽量压缩开支,借贷、典当也是农民在灾年最常见的应对手段。邓云特讲道:“农民遇年歉失所,朝不夕保,则其救济之法,自以保命为先。”(41)于是,农民会通过向亲友、富户等有余力者借贷的方法暂时缓解危机。但很多贫民因没有偿还能力而难以借贷(42),农民首先会典当衣物等暂时可以不用的物品,有时甚至出现“典去布襦几时赎,裤露两尻跣双足”(43)的情况。但借贷、典当也可能给不法奸商提供趁机压榨的机会,常熟地方当铺就“名曰二分起息,实则倍利矣”(44),如果受灾较重,农民不得不典当田产、水牛等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这就会从本质上危及农民赖以自立的经济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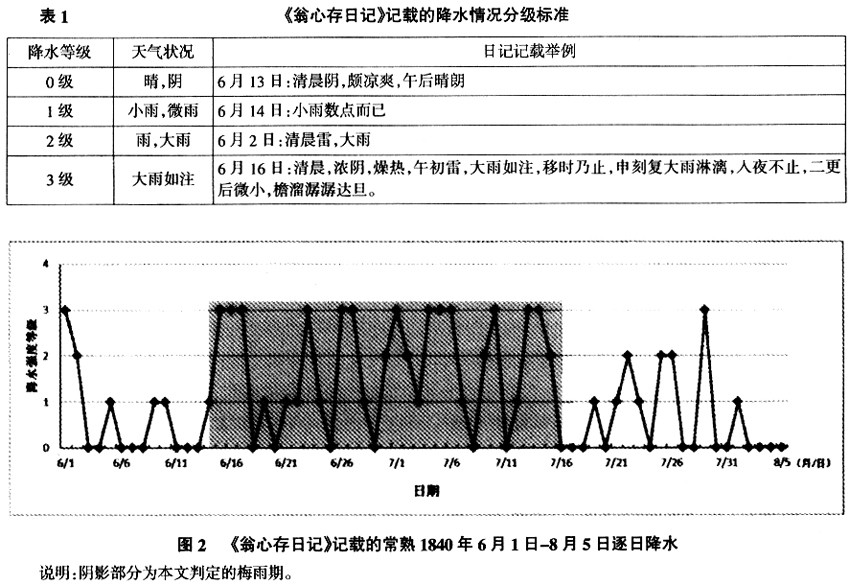 从灾害学的角度来说,农民的这些应对方式,本质上是将灾害损失在时间上往后推移,损失数量并未减少甚至还要增加,其灾后应对的实际效果则和受灾农民自身的经济能力有关系。在传统的江南社会,土地的兼并程度一直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在常熟地区,占总户数3.2%的地主、富户拥有59.5%的田地,而占总户数65.6%的贫农仅有22.4%的田地(45)。对于人多田少的贫民而言,必须兼做副业维持生计,这也是江南地区农业经济的特点(46)。 常熟作为重要的棉纺地区,纺棉织布是常熟小农经济的重要类型,“男女效绩,宿夜不惶”(47),而水乡地方的农民“操舟捕鱼”;傍山的农民“伐石担樵”(48)更是常见。这些谋生手段,使得常熟地区之民“不专仰食于田,故即遇荒岁,犹守妻子不轻去乡井,非其有宿储也,为谋生之方不出一途也。”(49)兼业虽然降低了农业在农村家庭经济中的比重,使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天气灾害的适应能力。但农村贫富的不均,实际上即是对灾害应对能力的不均,却不因这种兼业而改变。 因此,即便是普通农户在面对灾年时,也无力自己应对,而对于极贫的民众,以及一些没有稳定生计来源的短工,这就是“盖饥寒迫于身,始则流亡,必继为盗贼。”(50)他们“家无隔宿之粮”,一旦受灾,“朝不夕保”,极易成为流民,并通过偷、抢等不法手段获得生计,从而成为社会秩序中最动荡的因素(51)。而当普通的农民无力抵抗灾害时,他们也会通过“攒食大户”或者抢稻等暴力手段获得生存资料(52)。就是说,即使在一般的灾年,作为直接受灾的群体,也需要将灾害的损失,部分转移到社会其他群体中分担,这就造成了灾害影响在社会群体中的传递。 灾害影响在社会中的传递,首先是信息的扩散。从连降大雨到村民报灾,仅在几天之内。六月十一日《日记》记载“村民入县报灾者络绎不绝。”(53)信息由灾民传递到地方政府,而后又在地方士绅之间、士绅与政府之间以及基层社会间传递,这点在《日记》中多有体现。这种信息的传递使得每个人对于灾害及其后果都有自己的心理预期,这种预期将反映在个体的应对行为上。 水灾之初,时人认为当年水情已经接近1823年“癸未大水”的情形。癸未大水去时未远,对上次特大灾害的记忆加剧了民众对此次灾害的恐慌心理。谣言在散播。如六月二十四日“夜,晴,寇警频传,闻报尤乱,又有讹言大水将至者,城中颇多移居高乡以避之。”(54) 恐慌的心理易于引发激烈的行为。灾情初显之时,常熟地区就已经发生了多次盗匪事件,这些盗匪事件体现出民众的恐慌心理,并给士绅带来了心理冲击。《日记》于六月十一日记载当时已屡有村民抢夺大户的现象:“时乡民已屡有抢夺大户及舟行船板者,可虑也。”(55)同时,城中的抢、盗事件也给了翁心存为代表的地方绅士很大的震撼,他评价道:“城中如此横行,殊可骇异。”(56) 而随着信息的散播,灾害对区域社会不同人群的实际经济后果也开始扩散开来。作为直接受灾人群的农民,除了压缩自己能生产的主食消费,还会尽量压缩其他方面消费,如衣着、副食、世俗礼仪等方面,按照黄敬斌的研究,19世纪江南农家在这些方面的支出约占总支出的30%左右(57)。这部分开支的压缩,使得灾区的手工业、商业和从事各种服务业的人群生计也相应受到了灾害的影响。不仅如此,随着灾后信息的扩散,对灾害的预期也使得未直接受灾的人群不得不有意识地压缩开支,也使得社会的正常消费萎缩,进一步加剧从事这些行业人群的困难。而社会秩序不稳定,还会直接波及其经营。《日记》中记载了由于不逞之徒的抢夺,梅里布铺不得不歇业的情况(58)。 即使是处在社会上层的士绅,在这样的灾害中也会蒙受间接的经济损失。一方面,这些社会上层一般都拥有地主身份,并会对典当、商业等有投资。农业的损失,不可避免地要在其地租的收取上体现出来。而消费的萎缩,也会影响其商业的收入。更大的问题则是灾害导致的社会不稳对其生命财产的威胁。当年长江三角洲灾区多处爆发饥民滋闹事件(59)。在常熟,六月二十八日:“东乡低区圩岸多坍损,被灾较重,罟里村等处已有攒食大户者矣”。(60) 总之,1840年这场普通的水灾,在常熟地区,首先直接影响到了农业和农村,然后灾害影响又间接传递到社会各行各业之中。直接受灾的贫民,难以独立承受灾害的损失,需要社会各种形式的帮助。而有关灾害的信息扩散,以及灾民为生存而出现的激烈反应,则营造着社会紧张的氛围,促使社会各方面采取有力的措施,分担受灾群体的损失,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个过程就形成了灾害后果在社会中的传递。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