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古风古典时期的演变:被同性恋化和青少年化 从古风时期开始,同性恋风气在希腊形成和发展,至古典时期呈现出一种年长者和青少年结合的“老少恋”模式特征,⑩这影响了神话。至古典时代末,多位男性神明和英雄被塑造成至少拥有一名男性伴侣的双性恋,如宙斯、波塞冬、赫拉克勒斯和阿喀琉斯等。(11)对阿喀琉斯来说,他不仅被描绘为同性恋,且其形象也从中年人变成青少年,并由此衍生出“阿喀琉斯是否早死”的问题。 在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明显是异性恋,这从其宠爱布里塞伊斯和其母劝其找女人作乐可知。(12)此外,帕特罗克洛斯是阿喀琉斯最亲密的朋友,两人的友谊超越生死。(13)正因如此,两人的关系在同性恋风气盛行的古风古典时期被理解为爱情。(14)柏拉图在讨论其理想的爱情时,便高度赞扬了两人。他认为阿喀琉斯是个没胡子的青少年,并因珍惜和帕特罗克洛斯的爱情而被诸神送去福岛。(15)该说法明显受到当时“老少恋”同性恋风气和荷马的影响,后者交代了“阿喀琉斯比帕特罗克洛斯年轻”(16)和阿喀琉斯是“早死的”。由此衍生的问题是:阿喀琉斯是否是一位“早死的”青少年英雄? 即使在今天,阿喀琉斯也常被误会为一个青少年,包括荷马史诗研究者。(17)这一方面是因阿喀琉斯被青少年化后的形象被广为接受,另一方面是因荷马史诗有关其“早死”的记载饱受人们的误解。结合古希腊语文本,很容易看出这个“早死的”的实情。 在史诗中,有3个词用于修饰阿喀琉斯的早死。第一个是仅出现1次的“  ”(注定早死的):阿喀琉斯说佩琉斯本应很幸福,但身为凡人却娶女神为妻,后又被神明加害,“那就是在他的宫殿里,没有生下王子们的后代,反而生下一个注定早死的孩子。”(18)第二个是含“短命、短暂(shortlive)”之意的“ ”(注定早死的):阿喀琉斯说佩琉斯本应很幸福,但身为凡人却娶女神为妻,后又被神明加害,“那就是在他的宫殿里,没有生下王子们的后代,反而生下一个注定早死的孩子。”(18)第二个是含“短命、短暂(shortlive)”之意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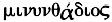 ”,在《伊利亚特》中出现6次,分别是阿喀琉斯对忒提斯说自己是短命的(I.352);西摩埃西奥斯因短命而死于埃阿斯枪下(IV.478);宙斯亲自保护赫克托尔,“因为他注定是短命的”(XV.612-613);希波托奥斯因埃阿斯的长枪而短命(XVII.302);吕卡昂向阿喀琉斯求饶时说自己是短命的(XXI.84);普里阿摩斯劝说赫克托尔进城时说,就算吕卡昂和波吕多罗斯被杀,特洛伊人只是“短暂的伤心”(XXII.54)。其在《奥德赛》中出现2次,分别是伊菲墨得娅的两个儿子“但生下短命”(XI.307);佩涅洛佩说“但凡人都是短命的”(XIX.328)。除“短暂的伤心”和最后的用法外,该词主要指死于非命的“短命”,是被外力杀死的结果。第三个是“ ”,在《伊利亚特》中出现6次,分别是阿喀琉斯对忒提斯说自己是短命的(I.352);西摩埃西奥斯因短命而死于埃阿斯枪下(IV.478);宙斯亲自保护赫克托尔,“因为他注定是短命的”(XV.612-613);希波托奥斯因埃阿斯的长枪而短命(XVII.302);吕卡昂向阿喀琉斯求饶时说自己是短命的(XXI.84);普里阿摩斯劝说赫克托尔进城时说,就算吕卡昂和波吕多罗斯被杀,特洛伊人只是“短暂的伤心”(XXII.54)。其在《奥德赛》中出现2次,分别是伊菲墨得娅的两个儿子“但生下短命”(XI.307);佩涅洛佩说“但凡人都是短命的”(XIX.328)。除“短暂的伤心”和最后的用法外,该词主要指死于非命的“短命”,是被外力杀死的结果。第三个是“ ”,意为“很快就死、带来快速死亡的、带来过早死亡的”。该词在《奥德赛》中出现4次,其中3次用于求婚者(I.265-266; IV.345-346; XVII.136-137)、(19)1次修饰箭矢(XXII.74-75)。其在《伊利亚特》中出现5次,除1处修饰箭矢外(XV.440-441),均用于阿喀琉斯。首先,忒提斯对阿喀琉斯说,“因为你的命运短暂,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现在你同时既会早死、又要比其他人更悲惨。因此,为了一个不幸的命运,我在宫殿里生下了你”(I.416-418)。(20)其次,忒提斯向宙斯哀求时说:“请重视我的儿子,他要比其他人早死”(I.505-506)。再次,阿喀琉斯执意要为帕特罗克洛斯报仇时,忒提斯说:“那么你很快就会死,我的孩子啊,你这么说的话。因为你的厄运会在赫克托尔之后立刻到来”(XVIII.95-96)。最后,忒提斯哀求赫淮斯托斯时说,“如果你将会愿意赠送我那快要死去的孩子以一面盾牌、一顶头盔、优良的与护腿相结合的胫甲和一件胸甲的话”(XVIII.457-460)。由此可见,上述3词共有6次用于阿喀琉斯,均出自阿喀琉斯和忒提斯之口。故而,阿喀琉斯的所谓“早死”,主要是忒提斯的想法、并影响了阿喀琉斯而已。这更多的是反映出母亲对儿子的重视和关怀,而非实情,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偏袒性、欺骗性和误导性。 ”,意为“很快就死、带来快速死亡的、带来过早死亡的”。该词在《奥德赛》中出现4次,其中3次用于求婚者(I.265-266; IV.345-346; XVII.136-137)、(19)1次修饰箭矢(XXII.74-75)。其在《伊利亚特》中出现5次,除1处修饰箭矢外(XV.440-441),均用于阿喀琉斯。首先,忒提斯对阿喀琉斯说,“因为你的命运短暂,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现在你同时既会早死、又要比其他人更悲惨。因此,为了一个不幸的命运,我在宫殿里生下了你”(I.416-418)。(20)其次,忒提斯向宙斯哀求时说:“请重视我的儿子,他要比其他人早死”(I.505-506)。再次,阿喀琉斯执意要为帕特罗克洛斯报仇时,忒提斯说:“那么你很快就会死,我的孩子啊,你这么说的话。因为你的厄运会在赫克托尔之后立刻到来”(XVIII.95-96)。最后,忒提斯哀求赫淮斯托斯时说,“如果你将会愿意赠送我那快要死去的孩子以一面盾牌、一顶头盔、优良的与护腿相结合的胫甲和一件胸甲的话”(XVIII.457-460)。由此可见,上述3词共有6次用于阿喀琉斯,均出自阿喀琉斯和忒提斯之口。故而,阿喀琉斯的所谓“早死”,主要是忒提斯的想法、并影响了阿喀琉斯而已。这更多的是反映出母亲对儿子的重视和关怀,而非实情,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偏袒性、欺骗性和误导性。其实,如果在阿喀琉斯死后、其子涅俄普托勒摩斯能立刻参战的话,(21)说明他并不年轻。此外,史诗记载赫克托尔之子阿斯提阿纳克斯是个“婴儿期的孩子”,(22)可见阿喀琉斯要比赫克托尔年长得多(安德洛玛克亦说亡夫赫克托尔还年轻)。(23)再考虑到赫克托尔是长子,这意味着普里阿摩斯所有儿女都比阿喀琉斯年轻。又如奥德修斯在阿喀琉斯死前已是一位“  ”(充满活力的老人),(24)但其子特勒马科斯在战后10年才长大成人,(25)即使考虑到晚育因素,他亦可能比阿喀琉斯年轻。此外,对这个可怕的敌人,特洛伊人及其盟友断然不会觉得阿喀琉斯早死,因为后者的存在是他们的苦难,(26)如普里阿摩斯就表达了对阿喀琉斯的憎恨。(27)更何况,军队主力是年轻人,论早死再怎么都轮不到连儿子都能参战的阿喀琉斯。这进一步说明近乎于博同情的“早死的”的说法,只是忒提斯及阿喀琉斯的一厢情愿,反映了母子情深,除此之外难以说明其他问题,但却影响了后世希腊人乃至现代读者。 ”(充满活力的老人),(24)但其子特勒马科斯在战后10年才长大成人,(25)即使考虑到晚育因素,他亦可能比阿喀琉斯年轻。此外,对这个可怕的敌人,特洛伊人及其盟友断然不会觉得阿喀琉斯早死,因为后者的存在是他们的苦难,(26)如普里阿摩斯就表达了对阿喀琉斯的憎恨。(27)更何况,军队主力是年轻人,论早死再怎么都轮不到连儿子都能参战的阿喀琉斯。这进一步说明近乎于博同情的“早死的”的说法,只是忒提斯及阿喀琉斯的一厢情愿,反映了母子情深,除此之外难以说明其他问题,但却影响了后世希腊人乃至现代读者。值得注意的是,若非同性恋风气的推动,单纯依靠荷马史诗的记载也许不足以使阿喀琉斯的形象被青少年化,这可从古希腊美术作品中推断。在古风古典时期的美术作品中,均出现无须或蓄须的阿喀琉斯形象,而胡子通常用来区分幼嫩的青春和完美的成熟。(28)在古风时代,阿喀琉斯的形象以有须为主,如一个阿提卡黑陶双耳瓶(约公元前540-前530年)的瓶身绘有蓄须的、形象与其他战士区别不大的阿喀琉斯攻击彭忒西勒亚的图画。(29)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中编号为“Harvard 1972.40”的阿提卡红陶提水壶(约前510-前500年),其壶身绘画主题是普里阿摩斯向阿喀琉斯请求赎回赫克托尔的尸体,3人均蓄须。此外还有几个古风晚期的陶罐,罐身绘画主题是蓄须的阿喀琉斯和大埃阿斯在下棋。(30)至古典时代,有须(31)或无须(32)的阿喀琉斯艺术形象同时存在。再对比欧里庇得斯在《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中提到阿喀琉斯有胡须(33)和柏拉图认为阿喀琉斯是一位未长胡须的青少年的说法,可见古风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其实并未最终形成“阿喀琉斯是青少年”的共识,但阿喀琉斯形象呈现出从中年人被青少年化的演变趋势则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可以推断,阿喀琉斯形象的被青少年化是荷马史诗的记载作基础、“老少恋”特色的同性恋风气所推动的发展结果。 结合上文分析,可见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是一个异性恋的中年人,但在古风古典时期同性恋风气尤其是“老少恋”的影响下,他和帕特罗克洛斯的友情被理解为爱情并被后人接受,(34)且因年纪更小而使其形象出现被青少年化的演变趋势。此外,虽然荷马史诗多次提及阿喀琉斯的“早死”,但远非实情。然而时至今天,阿喀琉斯那“早死的青少年英雄”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导致人们对其形象产生了一种同情性的误读。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