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恩格斯对族体与“王权”民族国家的认识 恩格斯比马克思更晚离世,因此他有更多时间在有关民族的认识论方面进行专门性研究。1884年,马克思逝世的第二年,恩格斯先后撰写了学术性较强的两部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 与此前的政论性文章不同,这两部学术著作涉及的民族概念更具系统性,术语含义更具一致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著作,就像其副标题宣示的,是“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是在摩尔根的唯物主义历史人类学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书中虽涉及“民族”和“族体”概念,但此两者却还不是作者想要探讨的主题。尽管如此,这部著作在解释“族体”的起源方面却贡献了宝贵的资料。 恩格斯在“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一节中指出,在日耳曼蛮族(20)征服罗马并不断扩张的过程中(5-9世纪)留下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一些现代族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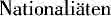 )的产生。后来在1891年的增订版本中,恩格斯又在该段文字下方有所增补,着重强调了日耳曼蛮族的氏族制度对新族体的诞生起到的决定性作用。(21)与日耳曼人形成对比的是,罗马帝国在被攻灭前,实际上已经具备了越过族体,直接形成新民族(Nation)的要素,但却没能形成新民族。这是因为“任何地方都不具备能够把这些要素结成新民族的力量,任何地方都还没有显示出发展能力或抵抗力的痕迹,更不用说创造力了”(22)。至于这是怎样一种力量和过程,恩格斯却没有展开论述。我们将会看到,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恩格斯回答了这个问题。 )的产生。后来在1891年的增订版本中,恩格斯又在该段文字下方有所增补,着重强调了日耳曼蛮族的氏族制度对新族体的诞生起到的决定性作用。(21)与日耳曼人形成对比的是,罗马帝国在被攻灭前,实际上已经具备了越过族体,直接形成新民族(Nation)的要素,但却没能形成新民族。这是因为“任何地方都不具备能够把这些要素结成新民族的力量,任何地方都还没有显示出发展能力或抵抗力的痕迹,更不用说创造力了”(22)。至于这是怎样一种力量和过程,恩格斯却没有展开论述。我们将会看到,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恩格斯回答了这个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讲,《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延续,在后者中出现的“新民族”将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被明确为“民族国家”。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恩格斯再次强调了族体的产生,并指出了族体与民族的演进关系:“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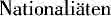 )”( )”( 是 是 的复数形式)(23),这种新民族,即族体的形成与语族的自然区分密切相关,语族一旦划分,“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 的复数形式)(23),这种新民族,即族体的形成与语族的自然区分密切相关,语族一旦划分,“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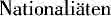 )开始向民族(Nationen)发展”(24)。恩格斯虽然没有为族体作直接界定,但是他却间接地表示,语言同一性是形成族体的关键。他紧接着说,“虽然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语言的分界线和国家的分界线远不相符,但是每一个民族(),也许意大利除外,在欧洲毕竟都有一个特别的大的国家成为其代表;所以,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的趋向,成为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25) )开始向民族(Nationen)发展”(24)。恩格斯虽然没有为族体作直接界定,但是他却间接地表示,语言同一性是形成族体的关键。他紧接着说,“虽然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语言的分界线和国家的分界线远不相符,但是每一个民族(),也许意大利除外,在欧洲毕竟都有一个特别的大的国家成为其代表;所以,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的趋向,成为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25)如果说在恩格斯看来,族体是形成民族的基础或先决条件,那么从族体走向民族的这种趋向是怎样形成的?或者说就像前文提到的,形成民族的力量是什么?为此,他详细考察了中世纪欧洲(封建)分封制的特点,认为分封制导致的分裂割据是阻碍民族统一或民族形成的屏障。他发现,封建贵族到中世纪后期“在经济方面开始成为多余,甚至成为障碍”,在政治上也阻碍着城市的发展,但是支撑贵族阶层的军事力量还存在。通过进一步挖掘,他找到了推动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两股主要力量:一是市民阶级崛起并与王权建立了联盟关系,这导致所有制形式从封建领主所有制迈向了市民阶级所有制,这是迈向纯粹私有制的重要一步;二是从14世纪初起,国王们为了摆脱贵族手中的封建军队,开始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原来服务于各个领主的军事力量转而为君主效力。(26)在所有制体制转变和军事力量集中的这两股力量中,王权均扮演了重要角色。 因此,恩格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27);第二,只有在君主制形式中才有可能存在民族国家。(28)这是他所考察的以15世纪末期为终点的历史阶段特点。 根据马恩对人类社会历史演进历程的考察,封建制度瓦解后,接踵而至的将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恩格斯却讨论了“从封建社会瓦解到民族国家产生”之间的过渡,并未提及资本主义及其与民族国家之关系。可以认为,在恩格斯看来,15世纪末期既是封建社会瓦解阶段,也是民族国家的萌芽阶段,此阶段中,族体是构成民族的物质基础,族体的联合统一是民族的特征,而王权则是民族的代表与核心要义。这种基于人类共同体演进历程得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民族国家认识论,与毫不考虑历史基础与源头的公民民族观或族裔民族观形成了鲜明对比。而16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发展,直至最终推动“去王权化”民族国家(或曰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的这一历程则留给了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去探索和发掘。后来,正是列宁较为系统而明确地阐发了资本主义上升阶段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间的对应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
